如何透過《蕉風》思考馬華文學:序林春美論文集
◎黃錦樹

馬華文學的研究有一定的難度。即便是受過完整的學院訓練,也不見得能做出有意義的成果。考驗的不只是訓練,還有想像力、洞察力,解釋的能力與創造的能力,那幾乎和寫作一樣困難。不多的大馬在地研究者中,林春美、莊華興和黃琦旺都是出色的例子。
近年因老輩凋零,藏書散出,集中在幾間大學圖書館,資料取得已經比較不是問題,或許也因此對研究者帶來更為嚴竣的考驗。數十年來,馬華文學近乎沒有改善可能的貧困,常使在地研究者受到疑似的傳染──如果貧困也能傳染的話。「傳染」當然不是個準確的用語。馬華文學的貧困是雙重的,評論和它的對象(作品)二者誰也超越不了對方,成了「命運共同體」。之所以如此,當然是有原因的;那原因,當然是歷史的、政治的。
林春美這本收集了多篇優秀論文的《蕉風》研究專著,恰恰是透過具體的個案,為我們闡明困境是怎麼形成的。
《蕉風》是大馬最重要也最長夀的華文純文學刊物,它恰恰誕生於馬來亞建國的前夕;在左翼是王道的年代,相對於那種種殺氣騰騰的革命文學刊物,它代表著「非左翼」;前者重視「革命」,後者重視「文學」自身;在冷戰的年代,後者被指控「綠背」(美援),而前者背後無疑有中共(有形無形的協助),紅背對綠背,兩者都深深的捲入政治。
把文學的美學面向視為頹廢,而以近乎絕對禁欲的態度操作名之為「文學」的事物,不知道自己行徑等同於自毀的革命文學陣營,沒能留下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品,應該說是毫不奇怪的。反之,雖歷經作風和理念不同的編輯,依然守護著文學自主性的《蕉風》(六○年代左翼馬華文學史教父方修在撰寫逐年的文學回顧時,可是直接把《蕉風》及其出版品略過去),倒是為馬華文學留下可貴的遺產。《蕉風》因此可說是「非左翼」馬華文學史的一個縮影。透過它,可以看到一個和左翼觀點截然不同的馬華文學史。
因為創刊於馬來亞建國前夕,對那「當下現實」的回應便是該刊物存在的理由。因中共建國而離開中國的那群知識份子,輾轉南下,恰逢南洋新興民族國家在肇建中,以他們豐富的學養和見識、敏銳的觀察力,很快就瞭解即將到臨的這國家的根本問題是甚麼,那比「本土化」更具反諷意味的「馬來亞化」意味著甚麼:
在作為國家的馬來亞正式誕生之前,文學雜誌《蕉風》已通過其編輯理念之實踐,讓我們得以窺見其對馬來亞國族「共同體」的想像。[……〕《蕉風》的「純」馬來亞化文藝之大纛,其實是建立在對馬來亞社會族群與文化多方面的「多元」性質的認知,及對其的渴求理解之上。(〈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
更根本的是,他們清楚的認識到,馬來亞化不等於馬來化,而主張各民族平等,共同創建馬來亞國族(左與非左翼皆然)。但那畢竟只是理想,甚至可以說是一廂情願。樂觀的氛圍一閃而逝,春美在針對那些年《蕉風》上的隨筆,編輯意見,甚至小說(方天〈一個大問題〉,姚拓〈七個世紀以後〉,申青〈無字天碑〉)的仔細分析,得出相當有說服力的結論:
對於源自中土的新客文人而言,馬來亞化──或說,實際融入馬來亞──最大的難題,在於族群政治及日漸形成的馬來霸權對於移民社群的排擠。(〈非左翼的本邦〉)
這批最後的南來文人已明顯的看到此後數十年這民族國家內少數族裔即將遭逢的難題,宗教、族群關係和馬來霸權將是不可跨越的高牆。在那樣堅硬的現實之下,「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即將被框在自己的族群內,不論是左與非左的「愛國主義文學」的口號,左翼升級版的「愛國主義的現實主義」、「愛國主義大眾文化」,只要不是用馬來文寫作,都是徒然的,更不必奢談甚麼「為人民服務」。建國後,大馬華人左翼大概沒有意識到,「人民」是他們最接近自瀆的幻想虛構。「有意淡化因種族、文化、宗教等的分歧而產生矛盾的現實」更是強調「反映現實」的馬華寫作人「愛國心」的體現。那「不可觸的」的限定一直延續到當代。
作為純文學刊物,《蕉風》最重要的功績是引介文學新思潮、世界文學、提供新人嘗試的舞臺,捍衛文學的獨立性。歷屆主編都能編能寫,有理念,也有創作能力。《蕉風》的創辦者之一,一個在星馬只短短的幾年居留,卻為馬華文學史留下寫實的經典《爛泥河的嗚咽》;謎樣的方天,「馬來亞化」的問題就在他任內提出(〈想像方天〉);〈馬華現代主義的起始〉談的是白垚的「新詩再革命」,馬華新詩現代主義的始創。相較於左翼的集體主義,除了語言與形式的革新,時代性的著重之外,他們還強調「人的再發現」;那意味著回到個人,個體主義,「人的文學」。
〈黃崖與一九六○年代馬華文學體制之建立〉有為黃崖「平反」的意味,春美細密的論證了這位「《蕉風》在友聯時期在任最久的編輯」,是「一九六○年代新馬華文學體制建立的關鍵人物」。他創造、引領、深化議題,「黃崖時期對文學自主法則的高度推崇,塑造了六○年代《蕉風》的兩個重要特質:一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引入,二是作為『純文藝』刊物的定位調整。」而它在文化主導權上的對手,當然即是不認為文學是自主場域的左翼。白垚「新詩再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裡展開的。換言之,〈馬華現代主義的起始〉其實可以說即包孕在這篇關鍵性的黃崖專論裡,同樣包孕在裡頭的,〈一九六○年代《蕉風》現代派的兩個面向〉討論的是六○年代張寒與梁園在《蕉風》上發表的系列「現代小說」。相較於現代詩,這是較少受學者關注的領域,尤其是放在《蕉風》推動現代主義的脈絡來審視。從春美的討論(包括論黃崖文對黃崖小說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馬華現代小說本身的艱難歷程──「馬來亞化」(回應「當下現實」)、現代感(實驗性)、可讀性(故事性、通俗性、「大眾化」)這各種要求之間,很難取得平衡。黃崖、張寒、梁園都各有所偏,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整體而言,成功的例子相當少。這結果很發人深省,尤其相比於馬華現代詩,現代詩的成績總體而言較為可觀。小說有通俗的天性,但強烈的現代感或現實感卻常會犧牲可讀性。因此,在小說寫作上,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面對的困難可能是相似的。
以純文學/現代/馬來亞化為標榜而比馬來亞還年輕兩歲的《蕉風》,只發表中文作品,讓它無可避免的被限定在華人的圈子,被民族化,也與大馬華人的命運緊緊捆綁在一起;它的生命歷程,一定程度的見證了華人在這民族國家的處境。不同作者發表的作品,編輯們的文學經歷,似乎也因此有某種象徵的意味。
〈《蕉風》吹到大山腳〉針對七○年代崛起的,幾個出生大山腳的年輕小說家發表在《蕉風》上的作品,春美觀察到五一三後馬華小說呈現出微妙的變化。那些現實感很強的現代小說色調昏暗,充斥著虛無感,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受到現實的擠壓和傷害。這當然不只是七○年代,當「馬來至上」成為這國家的根本原則後,在固打制下被擠壓的民族空間裡,文學似乎更不被需要,五○年代《蕉風》那些南來文人夢想中的、多元文化共存的「馬來亞化」,早已成了夢幻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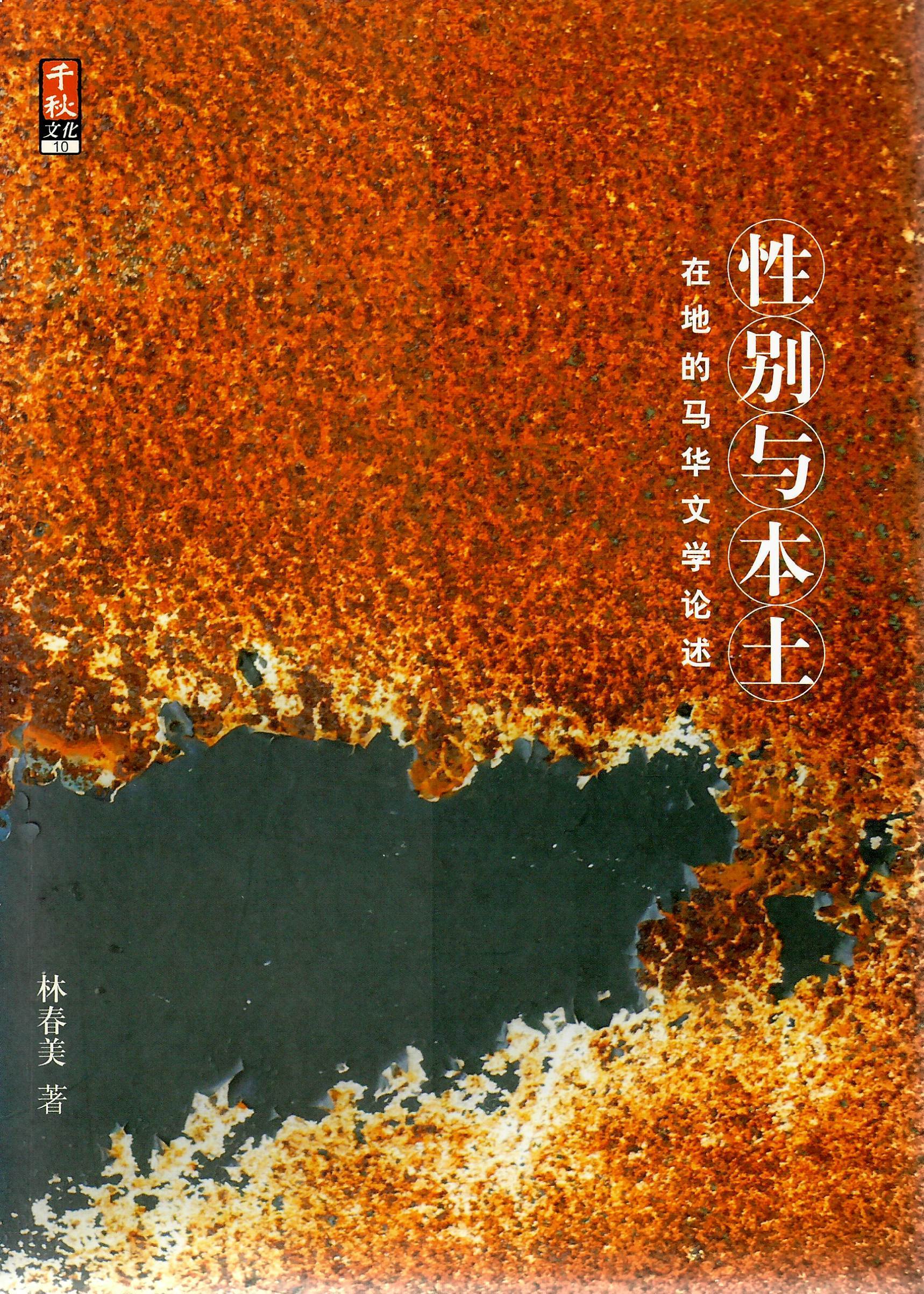
林春美《性別與本土》書影
身世成謎的方天,最終不歡而散的黃崖,相當有創造力的白垚,是「有國籍的馬華文學」擘創者。但身為無法獲得大馬國籍而被迫離境的一群人,他們的處境因此也成了「民族寓言」;作品也只能是一種「非國家-民族文學」,反諷的體現了早年理想化的「馬來亞化」在現實裡的「落漆」型態。〈身世的杜撰與建構:白垚再南洋〉仔細的分析了白垚的文學遺產、文學志業,在移居美國的晚年,以書寫重返南洋,重返那充滿可能性的馬來半島的五○年代,他的黃金時代,那個遙遠的「此時此地」:
從一九九○年代末至他驟逝為止,繼回憶錄散文之後又沉浸於自傳體小說書寫的十餘年間,持續的回顧使白垚在一定程度上把過去帶回到現在,因而也將夢──他的「夜來幽夢」──變成了生活/現實。因此,儘管南洋已遠,白垚生命最後十多年的時光,卻可說是他『再南洋』的一次經歷。
文學大概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它往往不能改變甚麼現實;它的時間,不是「此時此地」而是「事後性」,是追憶,是尋回失落的時光,是替代性滿足,也是一種撫慰。
──────────
黃錦樹,國立清華大學中文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與真理的技藝:當代中國小說論集》、《文與魂與體:論中國現代性》、《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等,另著有小說集《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等多種。近著有隨筆集《時差的贈禮》、小說集《民國的慢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