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是如何煉成的: 彭鏡禧教授訪談錄
主訪人◎單德興
時間:二○一九年十一月五日、十四日
地點: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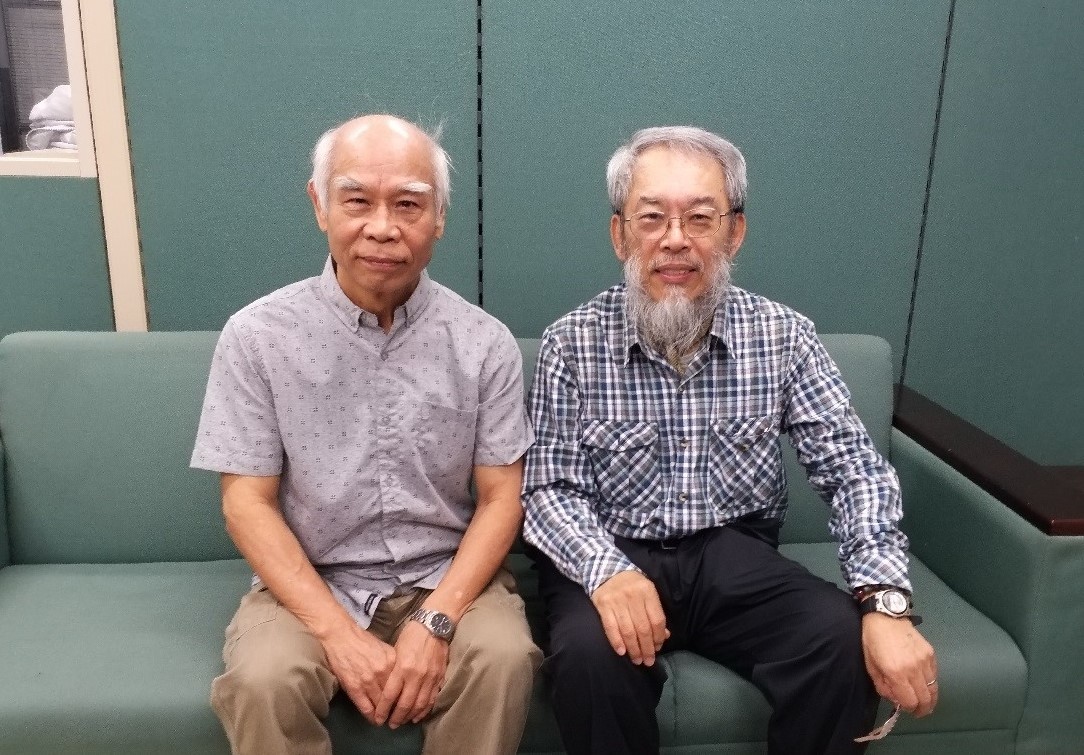
彭鏡禧(左)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於臺大接受單德興訪問。(單德興提供)
|家世與成長背景
單德興
請先談談你的家世與成長背景。
彭鏡禧
我的家世非常普通,父親彭達煌是新竹人,母親黃庚妹來自苗栗獅山村,就在獅頭山那個地方,雙方都是客家人,也就是新竹跟苗栗兩個客家家族的聯姻,所以我常會想到客家作家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我母親的家境在當地算是小康,舅舅是村長。那時候女孩子是不念書的,但是她對自然界各種植物類懂得很多,連我的弟弟彭鏡毅,先前服務於中研院植物所(現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他大學時候不認得的植物還要向母親請教。值得一提的是,我母親不識字,這一點現在回想起來,可以說對我的翻譯啟蒙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幫助。
我一九四五年出生於獅頭山,那時候二次大戰剛結束。後來父親在臺大擔任職員,全家就從新竹搬到臺北。我母親生了五個男孩、五個女孩,活下來的有九個。這麼多孩子,卻只有父親一人工作,所以家境頗為拮据。在那種環境下,大家的經濟狀況都差不多,因此小孩子都訓練得比較能幹,或是幫忙做一點家事,或是到外頭打個工,在那個時代這是很自然的事,並不會覺得特別辛苦。
|小學與中學
單德興
請談談你的求學過程。
彭鏡禧
我一直到出國念書以前,都在臺北古亭區求學。小學是念古亭國民學校,就是現在的古亭國小。那時候很少小孩念幼稚園。父親在我進小學之前曾帶我去北師附小考幼稚園,我記得他騎腳踏車載我去,考智力測驗。可是沒有錄取,顯然智商不夠。
單德興
那時候就有智力測驗?
彭鏡禧
那時候就是憑智力測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規的,總之我沒上就是了。記得父親安慰了我一下,我懵懵懂懂什麼也不知道。我快七歲時才念小一,因為新生入學(六足歲至未滿七歲)學齡區間為九月二日到隔年九月一日,而我是十一月出生,不能提前入學,班上有的同學是八月出生,我等於比人家大了快一歲。那時候班上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是像我一樣年紀大一點的。長大之後差幾個月沒什麼,但在小時候多少有影響,因此我從小就比較老成。
我小學念書念得不錯,是比較用功的學生,老師交代寫一行,我會寫兩行,也就是《禮記‧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的這種想法,會自動多做一點,我相信勤能補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時候家徒四壁,牆上掛的可能是明星或藥廠的大月曆,要不然就是一天撕一頁的日曆,或者藥包袋。我們家的牆上除了前面那幾樣,還有就是孩子們的獎狀。父親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我們在學校得了獎狀他就貼起來,貼得滿牆都是。「獎狀糊壁」是我印象裡很好玩的記憶,可惜沒有照相留影。
我的小學成績很不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初中時考上了建中。但是到了建中我就鬆懈下來,好玩,喜歡打球之類,結果考高中時僥倖進了師大附中。為什麼說進附中很僥倖?因為那年(一九五九)正好第一次實施「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如果按照以往,我的成績進不了附中,那麼走的路必然會帶出不同的結局。可是也因為那一年第一次實施新政策,以前市立中學的名額都跑到省立中學去了。三省中(建中、附中、成功)招的學生多了,我才能進附中。到了附中,當然又有很多不同的際遇,對我影響很大。所以我常說,人生有一些是不能選擇的,譬如原生家庭,可以抉擇的是:當你遇上了機會,怎樣使用它,這會影響到後面的發展。
單德興
那個時代都是到初中才學英文,你的英文造詣這麼好,聽說中學時就在英文方面下了很多工夫。
彭鏡禧
我的確喜歡語文,包括英文,但是我的英文造詣沒有你說的那麼好,我只是真心喜歡。當然,有一些老師的影響也很大。先前提到我的原生家庭是客家人,在家裡講客家話,平時的環境中又有閩南、外省等等南腔北調,所以耳朵變得比較靈敏。學起英文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有興趣。那時候學習語言的環境不如現在,除了學校,有的就只是趙麗蓮等教授發音主講的黑膠唱片,家裡也不是每一次都買得到,我們就邊聽、邊模仿。我喜歡背誦一些課文,像是美國麥克阿瑟將軍在國會大廈的告別演說〈老兵不死〉("Old Soldiers Never Die,"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Farewell Address to Congress, 1951),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吾愛美人不愛江山」的退位演說(King Edward VIII's Abdication Speech, 1936),我覺得寫得很好,就會去背誦。那時候我是騎腳踏車到建中和附中上課,會邊背邊騎,如果一時背不起來就停下來,拿書出來看,再繼續背、繼續騎。現在回想起來,的確是興趣使然,因為沒有人規定要你這樣做,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興趣很大,感謝上蒼!
單德興
後來大學聯考填志願時,臺大外文系是你的第一志願?
彭鏡禧
是。這裡面又有一個僥倖。高中時我真正的第一志願是法律系。法律系在我考試的那一年錄取分數是三九一分,比外文系低十分,外文是四○一分。我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我考的成績就是四○一分,是臺大外文系錄取的最後一名。填志願時我跟家裡人講想考法律系,父母沒有意見,可是有個在政府機關做事的長輩說,以我們的家世去考法律系並不好,將來沒什麼出路。因為當時的老立委訂了一個法,可以讓他們任職三年以上自動取得律師資格,因此每年能夠考上律師資格的不過六、七個人。所以我就選了外文系為第一志願。當時只填了二十一個志願,前三志願是臺大外文系、臺大法律系、臺大國文系,其他隨便填,最後一個是師大童子軍專修班,只要念兩年。那時考慮到學費的問題,所以填的都是公立學校。
其實,四○一分能夠上臺大外文系還有更多的僥倖。臺大那時候預定招收七十人,其中有些名額是給僑生的,那七十人裡面本來沒有我,因為之前已經有三人保送,實際應該收六十七人。當時分發是在臺大舊總圖書館,各系系主任或代表一起按分數高低錄取,名額滿了就輪到下一個志願。結果外文系分發到了四○一分時,有幾個人同分,全部收的話會超收,不收的話又會少收。由於那時候錄取率很低,乙組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幾,因此教育部規定:公立大學遇到同分的情況必須超收,私立學校則不得超收,所以我是在那種情形下超收進來的,而且在超收的幾人當中排名最後。我記得非常清楚,我的學號是七十二,531272,民國五十三年考上,1是文學院,2是外文系,72是最後一名,就是扛榜。
單德興
「孫山」。
彭鏡禧
對,所以好像有一隻手在牽引著我。如果少一分進了法律系,我會怎麼樣?會到火燒島嗎?
單德興
說不定選總統呢!
彭鏡禧
哈哈!
大學時代
單德興
你進了臺大外文系之後呢?
彭鏡禧
回想起來,我很高興進了外文系,進了外文系之後大致順遂,真是感謝上帝,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得非常愉快。
單德興
除了對英文很感興趣,是不是也對文學和寫作有興趣,來外文系如魚得水?
彭鏡禧
我確實喜歡文字,小時候也曾經參加各種作文比賽,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在寫校刊,像是《建中青年》、《附中青年》,甚至投一些小稿子到副刊。事實上我那年考上臺大主要是靠國文成績,那年國文比較難,我考了八十三分,憑那個成績可以轉臺大中文系,拿一萬元獎學金。
單德興
其他科目考了幾分?
彭鏡禧
記得不準確了。英文七十二吧,地理七十幾,歷史、數學、三民主義都五十幾。
大一時我加入大學新聞社,開始做校園記者。我印象很深,被指派訪問校長錢思亮先生,他人非常和氣,還贈我「不欺暗室」四個字,這對於我非常重要。過了一陣子,要為新生特刊採訪我的系主任英千里先生。他身體不好,我就到他的宿舍。當時他腸胃不好,躺在床上靜養。他問我稿子要用英文還是中文?如果用英文,就請顏元叔老師替他寫;如果用中文,就請侯健老師替他寫。我雖然沒有實際採訪到他,卻因此得知在他心目中,系裡英文最好的是顏老師,中文最好的是侯老師。當時顏老師剛從美國拿到學位回來教書,應該是副教授,侯還是講師。因此我一、二年級還沒上過他們的課,就知道他們兩位了。因為只得到這兩條獨家消息,當然就沒有登出來。由於《大學新聞》是中文刊物,所以我又訪問了侯健。
後來我在大學新聞社當編輯和主筆,印象最深的就是跟總編輯跑印刷廠。因為出刊的時間很趕,常常要當場校對,就在一旁看撿字工人穿梭在昏暗字架前快速地撿鉛字。他們本事很大,一邊看稿一邊就找出鉛字放進盒裡。檢完後交給排版師按雜誌規格排字、設計版面。那時候文章寫得最多的幾位當中有電機系的張系國,他在大四時發表了一篇〈孔子之死〉。我印象沒錯的話,那篇文章使《大學新聞》停刊了一陣子。1
單德興
那時候孔子的後代孔德成是不是在中文系教書?
彭鏡禧
應該是,可是我對他沒什麼印象。
單德興
編輯《大學新聞》是課外活動,正式的外文系課程有沒有哪些印象比較深刻的?
彭鏡禧
老實說,那時候的課程並不怎麼樣。幾門比較重要的文學課,教材都是油印的,像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長篇小說《浮華世界》(Vanity Fair)就是打字、油印發給班上的。那時候老師的學術訓練和現在不一樣,並沒有特別傑出。我記得英國小說課是依學號分配,不能自己選。我的小說課排到的是曹永揚教授。我想去侯健教授的班旁聽,但他的口音我聽不懂,只好作罷。隔壁班同學上張心漪的小說課就覺得很好,因為他們採用閱讀分組討論。聽說張老師的小說還曾刊登在美國的著名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呢。
大學的文學老師比較新穎一點的,大概只有黃瓊玖老師,她的戲劇課很有趣、很好玩。我是直到三年級上了顏元叔的「近代英美詩」課,才真的引發我對文學的興趣和對英文文學的瞭解。他用英文上課,教科書是 The Modern Verse,2 朗誦英美詩的聲音很響亮、很好聽。我三年級時(一九六六年)臺大外文系成立研究所,余光中先生在研究所教英詩,我去旁聽。余先生念詩、解詩都非常好,非常喜歡,受益很多。我畢業後服兵役,在中壢龍岡的陸軍第一士官學校,白天、晚上都帶著The Modern Verse到湖邊去朗誦,喜歡到這種地步。
四年級時的朱立民老師,他的教法又不一樣。他給你讀文學作品,然後選一個題目讓你寫一篇東西。朱老師教的不是美國文學,而是類似高階文學寫作(Advanced Literary Writing),只有經他挑選、各組寫作成績高的學生才能進來,一班大概十幾個人。
在寫作上,我受到美籍羅素瑛修女(Sister Ronayne)的大三作文影響很深,她教我們寫日誌(journal),一星期一次,就寫在英文報章雜誌上讀到的東西。我那時候常常寫關於《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上的社論,有一些發揮,她改得很仔細。大三結束的暑假,我到鳳山步兵學校去受分科教育。在那裡打野外很累,可是我每星期至少寫一封信給她,她也會回信給我。我們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師生情誼。我也帶了莎士比亞口袋書到鳳山,因為體力上非常疲累的時候,精神也會更加空虛。我還帶了一本《莎士比亞全集》(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一九五○、六○年代哈里森(G. B. Harrison)編的,墊在枕頭下。後來我到密西根大學讀書,戲劇教授告訴我,他的研究室就是當年哈里森使用的。
單德興
所以你是「三更有夢莎(士比亞)當枕」。
彭鏡禧
其實就是一種喜好,覺得那是很大的安慰。因為週末不可能從鳳山回臺北,時間與經濟上都不允許,就留在那裡看這些東西。
碩士班階段
單德興
什麼時候決定要考研究所?
彭鏡禧
三年級的時候,那時系上成立了研究所,我想說既然喜歡就繼續念。家父也是希望我繼續在臺大念研究所,然後就可以在臺大教書。臺大有個傳統,大四畢業公演是很重要的活動,因為上臺演出臺風要好、英文發音要標準,有很多高手都會參加。余先生的女公子余幼珊也參演過,她晚我許多屆,演的是《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她說背了很多莎士比亞的臺詞,很過癮。至於我們那屆演的是哪個劇本,名字已經忘了,後來經過同班同學裴耀立和喬令範兩位確認,知道是美國當代劇作家英奇(William Inge)的《琴瑟怨》(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喬令範還掃描了保存的招待券。我因為要準備研究所考試,所以只為這齣戲寫了英文劇情大綱(summary),沒有參與演出。
單德興
當時考研究所競爭很激烈?
彭鏡禧
因為剛成立,大家都不知道情況。那時候只有師大跟臺大有外文的研究所。
單德興
錄取人數多少?我們那屆是十二個。
彭鏡禧
好像也是十二個,我是第二名。第一名的陳典義,是從輔仁大學轉過來的同學。考試科目包括作文、翻譯、英國文學史和美國文學史。我的翻譯沒有及格,考了四、五十分。那份翻譯試題一看就知道是顏老師出題,中翻英、英翻中,文字裡有文學理論,也有他自己的觀點。我還記得英翻中有一題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後來顏元叔老師當系主任時主編「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要我參與翻譯。當時參與翻譯的大都是教授、副教授,至少也是講師,很少研究生,而研究生裡面我算是翻譯最多的。他找我翻譯的時候,我心裡很忐忑,問他:「我的研究所考試翻譯不及格,可以參加嗎?」他只嘿嘿一笑。3
單德興
我很好奇,那次考試的翻譯科目有幾位及格?
彭鏡禧
我沒有特別去問,但我猜想第一名的同學大概剛剛及格,其他可能都不及格。怎麼考核翻譯是一門大學問,或者可說是大偏見。有些人可能花很多時間可以做得很好,但在急迫的時間內會做不好。各種考量都有。
當時碩士班有顏元叔老師很熱情地推動文學研究。他覺得自己從美國學到了一些東西,所以組織碩士班研究生,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月會,鼓勵大家提論文來討論。我跟張漢良討論洛夫的詩,還寫了關於《石室之死亡》的文章。4 記得師大的陳鵬翔也來了,就在文學院二樓的大教室裡。
單德興
所以月會討論的題材並不限於英美文學。
彭鏡禧
對。事實上顏老師對於臺灣文學的發展很有一股很大的影響力。
單德興
他那時已經引介新批評(New Criticism)了嗎?
彭鏡禧
一開始就有,他還跟中文系葉嘉瑩老師有一些論戰。他先在淡江創立英文的Tamkang Review(《淡江評論》),在我當研究生時又在臺大創立《中外文學》。5他是一個doer(實踐者),也是開疆闢土的先行者。《中外文學》創始的過程有番小小的腦力激盪,就發生在朱立民老師的家裡。當時朱老師是文學院院長,做院長之初還兼了半年的外文系系主任,那是因為顏老師考慮了半年之後才答應當系主任。朱老師喜歡打撲克牌,那一年歷史系有一位美國客座教授,他太太在外文系義務兼課,朱老師就會請他們到家裡來打打撲克牌,有些助教也被邀去玩一玩。有一次晚上聚會,大家一邊打牌一邊就談到要開辦一份刊物,《中外文學》就是在那時候定下來的名字,但是英文要怎麼翻呢?後來就直接叫“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前面提到當年外文系的大學部課程其實不怎麼樣,顏老師來了以後,解救的方法就是新批評。新批評不是那麼重視作者的背景,而是談texture(字質)、irony(反諷)、paradox(弔詭)等等,這些東西很吸引我,因為以前念書時沒有這樣的東西。朱老師並沒有強力推動新批評,可是也沒有反對,他自己做的一些研究也跟新批評有相似之處。顏老師還透過各文藝刊物發表文章,造就了臺灣新的文學時代,影響力無人能及。
那個時代的文學氛圍非常蓬勃,很重視文學,高信疆主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瘂弦主持《聯合報》副刊,兩大報競爭得很厲害。如果今天一方登了顏老師的稿,另一方也一定會向他要一篇。顏老師有時候忙到進了辦公室把門一關,寫完之後交給來人,第二天就發表了。我也見過《中央日報》副刊的梅新在那邊等著要稿子。我們助教閒談的時候,都覺得顏老師好像是當今的約翰遜(Samuel Johnson),文壇的霸主。雖然新批評在美國一九七○年代之後沒落了,但它對我的影響很大,當時讀的《文學入門》(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好像就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和華倫(Robert Penn Warren)合編的,都是新批評的觀點。
單德興
李文彬老師後來到政大教「文學作品讀法」,也是用The Scope of Fiction跟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都是雙葉書廊盜印的。
彭鏡禧
那時候已經有盜印本,讀起來比較方便,之前用的是油印。
單德興
研究所階段有什麼課程讓你印象比較深刻?
彭鏡禧
研究生除了上課以外,考試很多。把英美文學分成七個時期,大概要選考四個還是五個時期。我選的有中世紀,其他的忘記了,好像也有美國文學吧。
戲劇方面我讀了莎士比亞。有一位菲律賓來的神父Father Bernard,是耶魯大學博士,記得曾經擔任菲律賓大學的文學院院長。為什麼要強調是耶魯大學博士?因為那時候師資比較缺乏,朱老師、顏老師來了以後,才慢慢多了一些比較注重文學、訓練比較好的老師。Father Bernard來這邊擔任客座教授時,我上過他的課。他是很好的學者,文章在《莎士比亞評論》(Shakespeare Survey)這類的刊物發表過。他講莎士比亞,也會談自己寫的文章,我從他那兒學到了很多。在他的研討課(seminar)上,每位同學負責一個劇本,我負責的是《李爾王》(King Lear),期末報告也是寫《李爾王》。我因為是研究生兼助教,外國老師來,會負責幫他處理一些行政事務,所以跟他很熟,他人非常好。那時胡耀恆老師剛從美國回來,開的是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戲劇,只有漢良和我兩個人選課,後來我翻譯出版了布萊希特的兩個劇本,要感謝胡老師啟蒙。6
喬叟(Geoffrey Chaucer)是我跟文彬、燕生三人都要考的作家,他們兩位上過郭博信老師的課,我則是自己讀,所以我們下了課會留得很晚,特別是要考試的時候會在一起研究。喬叟裡面wheel structure(輻軸式結構),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他們兩位,特別是文彬,都記得很熟。他們可以把故事從前面講下來,也可以從後面講上去,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還有若是跟其他同學一起讀書,讀得很晚,就到臺大夜市吃一碗麵。有時候一起吃個火鍋,一定要把湯喝完,沒有任何浪費。所以那時候有一些好朋友一起讀書,一起吃喝。
單德興
所以就跟夏老師一起讀書讀到現在?
彭鏡禧
(笑)對,是有這樣的機會。
單德興
碩士論文寫什麼題目?
彭鏡禧
我寫的是美國小說家華頓(Edith Wharton),題目是 “Edith Wharto' s Major Novels: A Structural Study”,選了她的四本小說,討論結構的問題,由朱立民老師指導。我覺得羅素瑛修女為我的英文寫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也從朱老師那裡對於 style(風格)有了一些認識。華頓師承詹姆斯(Henry James),詹姆斯常寫十九世紀末歐美上流社會的生活與人事(浮世繪),華頓也是這樣。詹姆斯的風格太繁瑣,華頓的比較容易學。後來我從美國回來以後,把這篇碩士論文大濃縮改寫成三、四十頁的 "Reappraising Edith Wharton"(〈重新評價華頓夫人的小說〉),發表在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的期刊。7
|攻讀博士學位
單德興
後來如何決定要出國攻讀博士學位,而且選擇去密西根?
彭鏡禧
這中間也很有趣。我當研究生的時候,應該是一九七一年,顏老師辦了臺灣第一次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在淡江舉行。8 他邀請很多國外的教授來,其中一位是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比較文學研究所的所長魏大可(Charles Witke),他的專長是古典文學,也當過文理學院副院長。他來臺灣,等於是臺灣跟美國比較文學學界的第一次接觸。
除了參加會議,顏老師也邀請魏大可到臺大談一談。魏大可說,在美國做比較文學的多半是西方人,少有東方人,更別說中國人;他希望顏老師推薦學生到那邊去做中西比較文學。顏老師就推薦我去。那時候我快要畢業了,也想出國,因為這邊沒有博士班可以念。家裡人,特別是我母親,不希望我出國。她覺得我現在是助教,拿了碩士以後就是講師,書讀那麼多幹嘛?而且出國留學要錢,我沒有獎學金是不可能出去的。我的大哥自費出國,很辛苦,借了錢打工,後來當然很好,在那邊工作。但他學的是電機,職業不成問題。我是學文學的,只能去申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需要經過學校推薦、口試、然後甄選。臺大推薦了兩個候選人,一個資淺的(junior),一個資深的(senior)。我只是助教,算是資淺的。口試時有中國老師、洋人(來臺灣的傅爾布萊特客座教授)。他們問我到美國要研究什麼?我說想比較中國小說和美國小說,因為我寫過一篇小說家華頓的相關論文等等。
傅爾布萊特獎學金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去研讀美國文學。我拿到了這個獎學金,就去密西根大學那邊拜見一位美國文學教授,談了一回,結果一門美國文學的課都沒選,都是在英文系跟東方語文學系上課。因為比較文學必須在不同的系修課,要有三種可以討論的語言,再加上一種可以閱讀的語言,所以我修了中國文學、英國戲劇、我自己喜歡的英詩專題,還有日文等等。不過他們也不在乎這些,反正你進來念,每年成績單送回去,表現很好就再給一年獎學金,最多給兩年,兩年後就得自己想辦法。因此我是以研究美國文學的名義出去,結果做了比較文學,而且側重在中國方面。
單德興
博士論文為什麼會選元雜劇?9
彭鏡禧
我剛去的時候,密西根大學的比較文學只有研究所,沒有大學部(現在也還是如此),研究所也沒有特設比較文學專業的教授,只有英語、斯拉夫語、法國、德國、拉丁、中國、日本等各領域選出的代表,組成Program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較文學學程),學生在老師指導之下選課。那時候東方語文的教授代表姓趙,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博士。魏大可就指派我到他那邊去,讓他當我的指導教授。跟我談了以後,他發現我對戲劇的興趣勝過小說。我當時不想再讀小說,覺得小說太長了。新批評的讀法講求細讀,要細細地看出什麼東西來。我沒辦法一天細讀個五十頁,一天大概細讀個十頁就很了不起了。這和我後來選擇做翻譯、讀詩都有關係。所以跟他談了以後,他說你也許應該去讀戲劇。當時我想,戲劇是介於詩與小說之間的文類,比較容易掌握(manage),加上我對戲劇也很有興趣,於是決定做戲劇比較。
決定之後我就開始選課。我在臺大外文系讀過一些西洋戲曲,研究所讀了莎士比亞,可是中國戲曲我只在高中時讀過一些散曲,在這方面根本談不上什麼基礎。指導教授推薦我去聽柯潤璞(James Irving Crump)的課,柯潤璞是美國頂尖的元曲學者,不但研究元曲、翻譯元曲,還把《戰國策》整個翻譯了一遍,是很知名的漢學家。他的念法就是細讀,對我來講壓力不大。我從他那邊開始知道中國傳統戲曲、特別是元雜劇的一些規律。還有就是他對於元雜劇中賓白的英文翻譯,他的英文翻譯非常的通俗(colloquial)、生動(lively),把元雜劇裡面的一些擬聲詞,什麼淅瀝嘩啦之類的,翻譯的非常到位。後來他也翻譯了很多散曲,出版了兩冊。我從他那邊學了很多,他會改我的文章。後來我決定跟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如果有幾個星期沒交東西給他,他都會來問:「你好久沒來了,我們談一談。」這個老師真的很好。
我還記得有一回碰到靈感枯竭、寫不出東西,他找我去坐他自己打造的雙人座滑翔機,親自駕駛,在安娜堡(Ann Arbor)上空兜了一陣子。這位老師是個奇葩,不像一般學者。他騎著大摩托車到學校,腰間總是掛一條手帕擦汗。他的興趣很廣,包括製作滑翔機。他買了材料,在自家的地下室開始刨,結果做好了抬不出來,只得把地下室的門拆了,再抬出來送進機棚(hangar)。他考了駕照,所以可以載我去玩。雖然就那麼一次,但我覺得這種真正關心學生的態度,對於我後來教書、作為老師的影響很大。我有很多恩師,他是其中一位。
回到你剛剛的問題,我為什麼選擇元雜劇作為論文題目?我去修課,看了很多有關中國戲曲的文章,發現傳統討論中國戲曲的時候,多半是把故事講一下,比較著重於曲唱和敘事的層面,一直到當時依然如此。像是臺灣第一位文學博士羅錦堂先生,他的論文把現存的元人雜劇整理出來,簡述劇情,然後分類,可是沒有像鄭騫教授談到曲的部分。曲的部分比較複雜,音樂方面我耳朵也沒那麼靈敏,所以我就還是在曲唱上面下工夫。研究結構,看如何從慣例(conventions)去創造(inventions),再看看西方戲劇理論,最後決定談元朝的公案劇,從元雜劇裡挑出十幾齣跟公案相關的──這可能跟我對法律的興趣有關係。
我寫了研究計畫(prospectus)就出去玩,誰想到暑假結束後在信箱裡看到老師留給我的一篇文章,正是討論元人雜劇裡面的公案劇!原來有人已經寫出來了,是由作者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刊登在當時最權威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0 那篇文章和我的計畫有很多的重疊。完了,大半年的功夫都白費了!後來跟老師再商量,把研究範圍縮小,論文名稱叫 “Judgment Deferred: An Intra-Genre Criticism of Yüan Drama”。Genre(文類)本身有各種東西,我就縮小到大概不到十個劇本來談,所以不必另起爐灶,只是縮小焦距,而且知道要快一點寫。
單德興
你的博士論文完成於一九七七年,一年後出版為專書Double Jeopardy: A Critique of Seven Yüan Courtroom Dreams(《一罪二審:評七部元代公案劇》)。11
彭鏡禧
那本書是由博士論文修改而成,這中間又有一番機遇。我出國進修名義上是公費出國,實際上是拿傅爾布萊特獎學金,等於是美國政府的錢。公費出國按規定可以留職留薪兩年,兩年後可以延長,最多到四年。那時候並沒有很嚴格執行這項規定,所以有人五、六年後回來,一樣可以復職。我的論文寫完時是第四年,便提出來要口試。研究所有一條規定,畢業學位口試前幾週,要先將論文送去格式檢查(format check),通過後才能進行口試。
我寫完論文後,心裡很輕鬆,就跟同學及燕生出去玩,回來要將論文送去檢查格式時,研究生院說對不起,期限已經過了,請等下學期。所以我下學期一開始就口試,記得那天是一月二十三日,自由日嘛,我覺得真自由。然而因為多了這一學期,超過四年,就有點尷尬,擔心回去後學校怎麼聘我。我跟朱老師商量,最後決定暫時留在密西根,他們再給我一學期的免學費獎學金,正好趕上翻譯亞里斯多德《詩學》(Poetics)的艾爾思(Gerald F. Else)教授於退休前最後一次開課。在此同時,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給我一個副研究員(Research Associate)的名義,好把我的論文修改到能夠出書的形式(book form),而不是目前學位論文的樣子。
單德興
那本書前面講到,以往研究元雜劇多是談詩意(poetic)或社會層面(socialist),而此書比較著重美學分析,討論元雜劇的語言和戲劇功能,特別提到研究方法是文本解讀(l' explication de texte),這等於是用新批評來研究元雜劇?
彭鏡禧
可以這樣說。我覺得自己的能力有限,也不太喜歡新的理論。比較文學的課程裡,有一位從歐洲來的塞德勒(Ingo E. Seidler)教授開了一門文學理論課,是我們的必修。那時候文學理論課有很多新的想法,一有新理論出現很快被推翻,可說是百家爭鳴。但是我覺得文學理論是為文學作品服務,為讀者服務,而不是反過來的。
前幾天密西根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來信說,他們最近獲得美國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梅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兩單位的補助,要把該出版社重要的作品數位化,我的書初步入選,所以寄來授權書。12 我知道了很高興。這本書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被奚如谷列為必讀參考書目。其實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從事文學與戲劇研究的人,比較少用這種研究方式罷了。
單德興
你客氣了!你是在那本書出版之前或之後回到臺大教書?是以副教授起聘嗎?
彭鏡禧
我在那本書出版之前就回臺大了,以講師起聘。那是臺大首創的新規定,新科博士以講師起聘,講師當一年,可以的話再升副教授。這個規定不是針對我,早我一年的鄭恆雄也是從講師起聘。我覺得無所謂,只是臺大要跟別的學校不一樣。
單德興
你等於是去了五年才回來,那五年都算留職嗎?
彭鏡禧
沒有,留了四年。第五年教育部突然嚴格執行規定,因為我拿了公費,所以臺大必須把我解職,要我賠一年的公費,賠錢之後再把我聘回來。在那個時候有很多關心我的師長,朱立民、顏元叔、侯健(當時的文學院院長)都幫我跟學校協商,讓我象徵性的賠一小筆錢了事,可是年資中斷了,只計算留職留薪的四年,第五年不算。我很感謝,少賠一整年的錢,那很多啊!我的運氣一直都很好。
單德興
也是因為很努力,才會有那麼多貴人相助。回國後主要是教哪些課程?
彭鏡禧
回來後先是講師,第一年教大一英文跟翻譯還是作文吧,還有英語聽講等必修課。之後也教了很多作文、翻譯這類別人不教的課。這樣也很好,訓練學生精確閱讀,對學生、對我都有幫助,打下了一些基礎。後來胡耀恆老師當系主任,鼓勵我教歐洲文學。他的意思是要培植我教文學課程,幫助我複習、再充實西洋文學。那時候學分很重,「歐洲文學」(上)(下)各六學分,我負責「歐洲文學」(上),從《聖經》開始教。這對我幫助很大,很感謝胡老師。那時候中文系的曾永義老師曾跟我提過兩人合開比較戲劇。這件事後來沒成,很大原因是系裡教書的負擔很重,臺大外文系要的就是能教西洋文學的人。
莎士比亞那時候有朱立民老師在教,有一次他出國開會叫我代課,好像是教《仲夏夜之夢》。因為我在臺大沒什麼機會教戲劇,而燕生在政大教書,所以金陵先生當政大西語系的系主任時,請我去教了兩年英國戲劇,教得滿愉快的。開莎士比亞課是後來的事。以前我對戲劇的瞭解全是書面的文學作品,後來轉到戲劇系是很大的轉折,開始思考更多演出方面的問題,也開始改編劇本。
|譯事:初試啼聲
單德興
你身為讀者,什麼時候開始跟翻譯結緣?
彭鏡禧
跟翻譯結緣不一定要透過閱讀書籍。現在回憶起來,跟翻譯結緣和我母親有關。先前提到我母親不識字,她的娘家在深山裡,那時候沒有電話,通訊靠寫信。舅舅或表親如果要來臺北也會先寫信通知。信來了以後,父親如果去上班,我就把國字寫的信用客家話講給母親聽。她要回信跟哪個舅舅講什麼,我就筆譯把它寫下來,像是她的代書。所以我的翻譯工作起步很早,從小學就開始了。
單德興
嚴格定義的翻譯作品是什麼時候?
彭鏡禧
大概在進大學前的暑假,我想找個工作,就常常看報紙廣告。有一次看到徵求翻譯,我就去應徵,被選上了。這是一份美國基督教刊物《標竿》(Guideposts),兩、三個月出版一期,小小薄薄的一本,英漢對照。主編皮爾博士(Norman Vincent Peale)是牧師,彭歌先生翻譯過他的《人生的光明面》(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皮爾是美國的主編,臺灣這邊的發行人是嚴以霖,他會定期寄稿子給我翻譯。那時候我還不是基督徒。這大概就是與翻譯結緣的開始,主要是賺一點稿費。
念了大學以後,我也常到當年的美國新聞處找各種書,因為那邊的英文藏書比較多。我特別喜歡看詼諧幽默的作品,一發現有這樣的書就借回來,覺得有趣的就翻譯,用筆名投稿《臺灣新生報》副刊,大概也譯過幾十篇,都是短短的。這是正式的翻譯工作。
單德興
那些投稿有留下剪報嗎?如果找出來,或許可以再出個中英對照的文集。
彭鏡禧
以前大概有,現在都不見了。不知道報社有沒有數位化留起來,有的話可以找出來,很好玩。
單德興
你常用的筆名有哪些?
彭鏡禧
換了很多,什麼澎湃、貞士、海(湖)濱客等等。有趣的是,有一天《臺灣新生報》的副刊編輯劉靜娟來找我,問我那些美國笑話都是從哪裡來的?我說是從美國新聞處借來的書上看到的。那時候《臺灣新生報》副總編輯暨副刊主編是童尚經,筆名童常,他太太華世貞就在美國新聞處工作。這是一個插曲。那些笑話雖然是補白,卻也引起了編輯的注意。
後來我在雙葉書廊買書,開始翻譯一些短篇小說,其中一篇是薩洛揚(William Saroyan)的小說,投給中油出的《拾穗》。13《拾穗》在當年是很好的刊物,介紹西方的科學、政治、經濟等,也有一些文藝資訊。我在那邊投稿,哥哥們看了也跟著投稿。所以我從大學時代就已經開始正式翻譯了,回想起來這些都是很好的準備工作。
我在大學時代不能說是求知若渴,不過就是喜歡去翻看一些新的東西。臺大附近有家長榮書店,書店的老闆張清吉先生不懂英文,但是懂日文,引進很多日本的書刊,也喜歡找人翻譯。之後他成立志文出版社,開始出版「新潮文庫」系列叢書,我常常去書店。有一天他問我:「這本 Irrational Man (《非理性的人》)你看過了沒?」我說這本書很好,主題雖然是存在哲學,但引用的都是文學作品,我讀起來很喜歡。他說,那你要不要試試看翻譯?我就翻譯一段給他看,他覺得可以,就讓我翻譯整本書了。14
那時候我大學四年級剛要畢業,畢業後當兵,很幸運地考上英語教育軍官,分發到中壢龍岡的第一士官學校,又分配擔任軍官班的老師。我跟張漢良、黎登鑫,還有另一位臺大外文系朋友王朱,四人同住一間寢室。我教軍官班跟教大學生一樣,一個禮拜上十二小時的課程,教材隨便我選。剩下的時間我就開始翻譯,一年後當完兵,《非理性的人》初稿也翻出來了。
當兵的時候還交到一位好朋友,就是教國文的教官王孝廉,他的兒子王震緒(筆名東山彰良)得過日本的直木賞。那時候我覺得《非理性的人》有一部分內容比較生疏,就把手寫的一段稿子交給他,請他幫我看。他的英文不好,但中文極好,是個小說家。他幫我看稿,不懂的地方畫個大圈,我就修得比較可讀(readable)了。
進臺大碩士班時書稿已經完成,但還沒付印。我當助教時認識了一些朋友,包括也是助教的陳凌霞,她先生葉新雲是哲學系講師,我就問:「葉大哥,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些哲學名詞、以及意義上有沒有錯誤?」他很夠意思,全部幫我看完,遇到有問題就幫我修訂。有了王、葉兩位校正,這本書不只可讀,錯誤也較少。
那時候存在主義非常流行。這本書先前已經由三民書局出了一個譯本《沒條理的人》。我拿來一看,它引述原文的部分,幾乎全都譯錯,所以我就不太擔心了。這本書對我後來的翻譯工作大有助益。出版後十分暢銷,再刷了很多次,印到最後紙版都模糊了。
張先生後來又要我翻譯紀德(André Gide)的《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我也透過這本書對歐洲的文壇史多了一點認識。15 有了實際的譯作,後來在學校裡,朱立民老師和顏元叔老師就叫我翻譯了很多作品。朱老師譯了一本新亞出版社的《美國劃時代作品評論集》(Landmarks of American Writing, ed. Hennig Cohen),我記得我翻譯了其中四篇,分別討論了艾德格.愛倫.坡(Edgar Allan Poe)、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惠特曼(Walt Whitman)、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16 這四篇都是討論文學作品,也大量引用文學作品,我非常喜歡。我還記得一個場景,就是朱老師為了要統一大家的作法,在臺大文學院二樓會議室召開了一個編輯會議,來了大概十幾位譯者,我是唯一參與翻譯的助教。他要我負責擬出編輯體例,比如標點符號的規範等等,讓大家根據共同的格式來翻譯。這些老師交給我做的事,給了我很大的信心,對我往後的發展和勇氣有很大關係。
單德興
你在《非理性的人》〈一九六九年版譯序〉裡提到,「翻譯之際,我自己的要求是使譯文明白暢達,但絕不曲解原譯。若做不到明白暢達,那翻譯的工夫勢必白費,若曲解原譯也算不得翻譯」,17 這跟你後來對翻譯的要求十分一致。
彭鏡禧
對。大概在那時候我就有這個想法,所以我會請王孝廉和葉新雲驗證(verify)內容與文字是否合適。
單德興
那本書很暢銷,有人跟你提過你的譯本對他的影響嗎?
彭鏡禧
很多。在很多學術界場合,人家會說,我讀過這本書。曾經擔任《民生報》主筆的陳曉林從大陸回來,說是在大陸看到黑龍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盜版。當年大陸對版權沒有什麼保障。我從美國回來以後,立緒的鍾惠民女士說要重新出版這本書。但是譯稿已經賣斷給志文(一千字五十元,總共二十萬字,所以稿酬是十萬塊,也不少了),我就去找張清吉先生,那時他半退休了,我告訴他志文的版本已經不合適了,現在有人想做這件事,可不可以讓他出版?我跟他講我可以給他一萬塊,張先生就答應了,但是沒有收這筆錢。立緒出新版時,我請葉新雲寫了一篇序言。18 這本書賣得還不錯,立緒還再版過,我從香港回來時收過幾千塊的版稅。
單德興
這本書的出版其實牽涉到臺灣翻譯史或者市場的問題,從前沒有智慧財產權法的時候,市面上可以有不同的譯本,彼此競爭,讓好譯本去淘汰壞譯本。現在有了智慧財產權法,當然是對作者和出版社權益的維護,但是如果所譯非人,出版社也不負責任,笑罵由之,市面上就只有這麼一個譯本,結果作者和讀者反而遭殃。
彭鏡禧
我倒是沒有這樣想過,但是的確有這樣的可能。假如我是出版社,要去買一本書的版權,當然是希望獨家授權(exclusive right),甚至是簡體、繁體字版權一併買斷,讓別人都不能做。不過即使不論獨家授權的情況,在臺灣的出版市場小,只要壞譯本先出來,好譯本通常很難生存,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除非後者好得驚人或者前者爛得太明顯,不然後來者很難生存。
單德興
如果翻譯的水準相去不遠,先出版的確實佔優勢。但是像你這本和另一個譯本差異很明顯的情況下,口碑或者譯評自然會淘汰不好的譯本。
彭鏡禧
這我不敢說,不過也許和這本書被一些學校選為哲學教科書也有關係,這些老師教一下就知道了。
單德興
除了文學翻譯之外,你也做了很多戲劇翻譯。前面提到顏元叔老師邀你參與驚聲編譯文庫的「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系列,那是非常大的一個計畫,稱得上宏圖大略。
彭鏡禧
對。這個系列對臺灣劇團、臺灣戲劇界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當時臺灣劇團的劇本不僅少,而且意識形態太重。顏老師的這個計畫真是大手筆,附屬於淡江大學的驚聲文物供應公司願意讓他放手去做也很了不起。那時胡耀恆老師還為這個系列寫了一篇長文,在《中國時報》連載了兩天。19 我們翻譯的這一套書到現在還有人在演,像是北藝大等藝術學校,曾經有學生來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沒有版權。這些書有的原文已經屬於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至於中文版權的所有人驚聲公司已經不存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單德興
參與這麼大的計畫,你有何感想?
彭鏡禧
當然是與有榮焉,交給我的劇本相當多,大概有五、六本吧?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終局》(Endgame),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The Good Person of Szechwan)和《高加索灰闌記》(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羅卡(Federico Garcia Lorca)的《白納德之屋》(The House of Bernarda Alba),還有辛約翰(John M. Synge)的《西方男兒》(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20
單德興
這是你第一次翻譯戲劇?除了要求通暢、正確之外,有想到舞臺演出嗎?
彭鏡禧
這是我第一次翻譯戲劇,至於搬上舞臺演出也是絕對有考量到的。我小學時演過戲,演一個逃學生,跟我演對手的是同班同學倪敏然,這是我第一次登臺演戲。剛剛講的正確、達意,我翻譯戲劇時就注意到每個角色講話的內容和語氣都不一樣,顯示作者怎麼表露一個人的性別、身分、年齡、職業、性格,這些都必須譯出來。至於文字的順序則是更高層次、更細緻的問題,因為中英文語法的不同或前後邏輯的關聯,要更合理、傳神。
這份工作也給我很多的訓練,中間顏老師還要我翻譯一些論文之類的,加上從前替張清吉先生翻譯的經驗,讓我對語言、還有自己的譯文要求提高,務求精確,對英文的文法結構也更加瞭解。所以我現在讀英文作品很慢,但比較少看錯。翻譯要求準確,必須精讀,而不是略讀。我非常感謝在研究生時期有這些機會,我相信這和我後來出國申請到獎學金有點關係。審查者看我的履歷也許會想,這個人竟然已經有了這些名著的譯作,而對我有信心。
單德興
翻譯劇本有時會牽涉到轉譯的問題,例如布萊希特的德文劇本經過英文的翻譯,不曉得你對這點的看法如何?
彭鏡禧
老實講,我當時並沒有這個意識,心裡知道自己翻譯的英文版是由德文、西班牙文轉譯的,但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另一方面,實務上確實不得不如此,因為當年沒有這麼多的人才可以直接從原文翻譯。後來我念了比較文學,知道這種作法有缺陷,因為翻譯就是一種詮釋,經過詮釋再詮釋,會離原來的作品更遠。我覺得自己日後不可以再做這種事情。
回來臺大後,有機會參加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的規畫案,當時找了一些人組成一個委員會──你也在裡面──決定應該翻譯哪些作品,我就表示要從原作直接翻譯,不要轉譯。這也是因為時代進步了,慢慢有一些能閱讀原作的學者出現。經典譯注計畫的譯作都是直接從原文翻譯過來,應該是比較合適的翻譯方法。所以我才請朋友、也是我們系裡的鄭芳雄教授來合譯《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闌記》,他是研究德國文學又專攻布萊希特,當然是翻譯這位劇作家最合適的人選。雖然說是我們兩個人「合譯」,其實我只是把自己從英文轉譯的中譯本交給他。不過他跟我說,我的翻譯雖然轉譯自英文,但誤解很少。這要感謝英文版的譯者,表示那個人翻譯得準確。
我希望把早期由英文轉譯的作品都改正,例如羅卡的作品,我請我的學生陳南妤來重新翻譯。她在我的翻譯課上做得很好,也精通西班牙文,到西班牙念了博士。她曾把她的作業,羅卡的三首詩從西班牙文翻譯成中文發表在《中外文學》。後來她申請到經典譯注計畫,出版了羅卡的詩選《吉普賽故事詩》(Romancero gitano)。但是《血婚》(Blood Wedding)和《白納德之屋》這兩個劇本好像還沒有人從西班牙文翻譯,很可惜。
我的翻譯後來跟戲劇、劇場連結,所以我知道譯文本身必須可以讓演員朗讀、演出。可是中文劇場,不管是在臺灣或大陸,似乎很少在語言節奏上有所訓練。原因是現在詩劇很少,不太重視語言的節奏,一堆電視劇演員的口條都不是很好,隨便上鏡頭講話就可以了。雖然大陸有些傳統劇場或劇團還是很注重表達,可是他們有他們的那一套,覺得表演莎士比亞有朱生豪的散文譯本就夠了。
我做過一個小小的研究,算了一下,一部莎士比亞詩劇用散文翻譯,每五百字就會比用詩翻譯多出大約一百字來。這些譯者不是不會精簡,而是一旦決定用散文翻譯後就放得很鬆,只求把話說清楚。我還寫過一篇論文討論莎士比亞戲裡文字的順序,例如兩個人物有段對白,主題是A、B;前者在兩人談論A的時候提及B,而且提到B時是用插入句的方式把完整一句話斷開來,以引起後者對B的關注,而翻譯時應當如何處理這個插入句,才能表現出作者刻意中斷所營造的延宕效果。21 一般研究翻譯的都是學者,與演出沒有關聯,我則會注意彼此之間的關聯。
單德興
那篇文章討論字序對於戲劇效果的重要性,主張要是忽略字序的話,戲劇效果就會打折扣。
彭鏡禧
是的。瞭解演戲方面的問題之後,就會稍微注意這些東西。
單德興
你在《威尼斯商人》的〈前言〉提過,你翻譯成中文之後會請夏燕生老師一起讀劇。
彭鏡禧
我翻譯完一個劇本,需要知道它能不能讀,我們兩人就拿著對讀。如果有點問題,就當場標示,再修改。
單德興
自己翻譯的譯文念起來會覺得比較順,請別人來念,是要幫你挑毛病嗎?
彭鏡禧
當然。實際上翻譯,特別是劇本,請受過愈多訓練的人來讀總是有幫助的。像是我最先翻譯《非理性的人》,就找了真的懂哲學以及文字好的人來幫忙。人難免都會有一些偏見,對於自己翻譯的東西,這個句子你覺得很順,但是別人可能不這麼認為。有了別人幫著看看、念念,總是好的。我翻譯莎士比亞,對譯文提供意見的還有余國藩、王裕珩、張曉風、陳芳、周力德、王瑋廉等多位教授或演員。很有幫助。
|翻譯的多元實踐
單德興
你在翻譯方面有多方位的呈現,除了從事翻譯,還教學、論述、編譯、評審,能否稍加說明。
彭鏡禧
翻譯的實踐就是去做,像《好詩大家讀》就是。22 我在美國的圖書館看了很多英美詩選,然後開始翻譯。剛開始翻譯時,並沒有想要出書,就只是喜歡。一九八六年九月聯合報系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中文版創刊,動員了北部地區很多從事翻譯的人,我負責修改、編輯。在那邊認識了楊漢之先生,他正主編一份《動象》月刊,建議我把這些譯詩在他那邊發表,有一次甚至一口氣刊出了十三首。除了《動象》之外,我還投到一些報紙、刊物,包括《中外文學》,後來看看篇數夠了,就整理成集子《好詩大家讀》。那是在我獲得梁實秋翻譯獎之後,所以才敢請余光中老師寫序。
單德興
第一屆(一九八八年)梁實秋文學獎你是翻譯詩與散文的雙料冠軍,之後主辦單位就規定,兩項都第一名的只能擇其一,我戲稱這是「彭鏡禧條款」。你那時怎麼會想要參加梁實秋文學獎的競賽?
彭鏡禧
因為那是第一次有重要的翻譯獎,我當然很重視,而且又是紀念梁實秋先生,意義非比尋常,於是就在想要不要投稿?我自己是臺大教授,如果投稿沒中,也許只有評審知道。但是如果朋友、學生得了第一名,我得了佳作,而自己還得教翻譯,是有一點顧慮,因此要有些勇氣才能投稿。你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也投稿過並且得過這個翻譯獎的首獎,是不是要有些勇氣?
單德興
我們不教書,壓力沒那麼大。
彭鏡禧
我考慮了很久,最後還是把稿子遞了出去,做人膽子要大一點!後來聽說我的翻譯本來不是第一名,是余先生斟酌之後才說服大家的。
單德興
你後來多次擔任過梁實秋獎的評審,而我參加過的三次評審,也是你出國,余老師要我來替補的。所有的投稿都是匿名,評審者完全是就翻譯論翻譯。余老師對每一首詩、每一篇譯文都仔細評審、打分數,所有評審委員中很少像他那樣看得那麼仔細的,所以能被他評為第一名的應該是當之無愧,雙料冠軍更是難得。
彭鏡禧
我常常跟學生講,這類投稿比賽,當然不知道誰是評審,如果評審決定了,大概就知道誰會是第一名。每個人有他的文學觀和愛好,翻譯也一樣。翻譯評審當然會有一些共識,例如不要隨便增加詩行,十四行就不要譯成十七行。不管是香港或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用白話文,因此就不能譯為中國的格律詩體。除此之外,有些地方我們會爭論很久,哪裡要扣0.5分之類的,這些牽涉到評審的審美。認真的讀者,他的偏好會影響到對作品的評價。
單德興
有人說翻譯可以教;有人說翻譯是一門藝術,沒辦法教。根據你的教學經驗,究竟如何?
彭鏡禧
也有一個說法:翻譯可以學,但不能教。我認為翻譯是可以教到一個地步,但再上去就不行了。我教翻譯的時候,就學王孝廉的那個方法,把學生作業翻錯或不清楚的地方畫起來,要學生自己再去對照原文。可是光是這樣還不夠,因為學生仍然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把我的翻譯給學生看。看看譯文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怎麼翻,然後再去對照原文。這是可以教的部分。但是我不願意一字一字的改,可能學生有他自己的風格,我在這地方改了,別的地方是不是也要一併改?若是全改了,那就不是他的翻譯了,所以我盡量避免逐字修改。我對學生的翻譯主要是要求正確,不過表達方法可以跟我不一樣。風格這個部分不容易教,恐怕也是不能教的,因為牽涉到閱讀的東西、對於美學的看法等等,因素太多了。
單德興
你在大學部跟研究所都教翻譯,教學方式會不會不同?
彭鏡禧
研究所比較重視對於翻譯的看法,還有就是討論別人的翻譯,訓練學生做個評論家。假定研究生在閱讀方面都沒問題了,也有一些翻譯的經驗。像是有幾位上過我翻譯課的學生,譯論寫得很好,我就推薦給《中外文學》。
單德興
我記得在《中外文學》讀過幾位高足的論文,包括王寵討論建築師王大閎翻譯王爾德(Oscar Wilde)的《杜連魁》(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等等。
彭鏡禧
是的。像是姜台芬、邱錦榮也上過我的課,他們在比較文學會議上發表過論文,談的是漢學家施友忠翻譯的《文心雕龍》。
單德興
我記得梁實秋曾經在文章中寫道,原先看《文心雕龍》有些不懂的中文,看了施友忠的英文翻譯反而懂了,這就牽涉到詮釋(interpretation)的問題。
彭鏡禧
對,譯者替我們詮釋,常常是這樣子。像之前我們看由莎劇改編的豫莎劇,陳芳教授寫的詞有的太深,有的含典故,看不太懂,但是看英文字幕就可以瞭解。
單德興
你的翻譯論述《摸象》於一九九七年初版,二○○九年的增訂版增加了第四輯「翻譯莎士比亞」。23
彭鏡禧
對,加了莎士比亞。初版原本只有評論和一些評審心得,包括討論你得首獎的譯文之類。24 這後來影響到我對翻譯寬鬆的看法。我們當然希望翻譯都是正確的,將原作表達得很好。翻譯可以簡化為閱讀加寫作,可是這中間就複雜了,你如何閱讀,表達出的是怎樣的寫作風格。我看到很多不同的翻譯,其實這些譯者的閱讀並沒錯,只是選擇的表達方法不一樣。譬如辜正坤翻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原文有七個韻,但他認為中國讀者不習慣頻繁換韻,所以他翻譯時就盡量以「一韻到底」為原則,但不一定做得到,而且他用的語彙(diction)比較接近詞曲。這樣一來,傳統的英詩節奏、抑揚都不能談了,因為譯文不一樣了嘛,但不能否認這還是一部很好的翻譯。25 我的堅持是:不管怎麼翻譯,只要可以吸收人家好的東西,然後自己重新轉換,出來的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那就夠了。
我常說translation的"trans" 就是 "cross",但跨界,就不一樣了。橘逾淮為枳,而枳有它另外的一種美。如果按著我起初對自己翻譯的要求,錯誤要減到最少,風格也要一致,還要附上原文給讀者對照,這種作法很辛苦。現在我的想法有所改變,是比較跨文化、寬鬆的一些看法,最近我在一個論壇做了專題報告,整理出來兩千多字,就是在談這個問題:跨文化作品必然是原創。26
單德興
這讓我想到你為嚴復紀念會議主編的論文集《文學翻譯自由談》。你在其中一篇〈文學翻譯隨想〉對目的論(Skopos theory)有些批評,認為在翻譯跟改編之間有一條界限。
彭鏡禧
那時候我還是覺得有,現在則覺得推得遠一點也無妨,因為翻譯也是原創。一旦改變了原作的文字,比如改變詩的韻腳、節奏,這些都是原創之舉。從最普通的翻譯一直到改編,都在原創的範圍。不過對學者來講,對照著原著看改編,常常會批評不忠實。現在創了一個名詞叫「衍譯」,翻譯可以延伸為「衍譯」,例如黃克孫透過英國作家費滋傑羅(Edward Fitzgerald)的英譯本《魯拜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以七言絕句衍譯。我覺得改編也可以延伸為「衍創」,放入更多自己的材料,事實上就是一種創作。
我舉《趙氏孤兒》為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邀請頗富盛名的英國詩人芬頓(James Fenton),將《趙氏孤兒》改編為The Orphan of Zhao,二○一二年十一月至隔年三月在莎士比亞故鄉的天鵝劇場(Swan Theatre)演出。The Orphan of Zhao 第一部(Part One)的情節跟我們一般知道的中國故事大同小異,但是第二部(Part Two)關注的焦點完全不一樣,它是放在孤兒本身。芬頓讓鬼魂出現,深入挖掘整個悲劇裡的各個角色,讓我們不只是看一個復仇故事。例如趙氏孤兒,程嬰讓趙氏孤兒認仇人屠岸賈為義父,但屠岸賈就算再壞,也養育了他十八年,而且對他那麼好,他怎麼下得了殺手?另外,這故事有一些延伸,對許多角色的心理有更多的延續與剖析,例如趙氏孤兒的母親,完成使命後的程嬰,還有程嬰之子才一個月就頂替趙氏孤兒被殺,他的亡靈會怎麼想?戲的最後出現一個小孩子的鬼魂,他說,母親,他們都叫我報仇,而趙氏遭到滅門的三百人都變成了鳥,在樹上飛。因此,傳統戲曲裡面沒有觸及的東西,芬頓都創作了出來,把這個故事現代化。
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要對當代的讀者有意義,戲劇也是。傳統戲曲喜歡頌揚忠孝節義,可是現在講這些人家都不愛聽了,即使要講也要用不同的手法來表達。我看了芬頓的改編,就真的覺得:「哎呀,這麼好的作品!」這部作品在中國大陸原已有人翻譯,有趣的是,他們想把它演成一齣音樂劇,就找了我們香港共同的朋友金聖華教授來翻譯劇本。金聖華說:「我沒翻過戲劇,你找彭鏡禧吧。」通常我們反對合譯,比如一本書拆成兩半、一人一半的作法,但是我跟金聖華合譯了這部作品。兩人分頭全譯,再互相批評,得出共識。這樣做當然辛苦些,但至少我有很大的收穫。27
單德興
你本人在翻譯上多元實踐,從教學、評論到推廣都積極參與。幾十年前余光中老師便呼籲要重視翻譯,尊重譯者。你也提到,從事翻譯者要對原作抱有同情與尊敬。領會到這一點的譯者,才能將原作恰如其分地翻譯出來。你如何評論當今譯者的地位與角色?
彭鏡禧
這個問題也談論了很久。我去美國念比較文學之後,開始對翻譯有一些想法,決定不要做二手翻譯。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投到《中央日報.海外版》,就是談翻譯地位的問題。我發現美國很多大學都有學術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我要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不是發現有一個人已經寫了同樣的東西了嗎?他的研究內容打字稿大概不到一百頁,可是附了三個劇本的翻譯,那時候他已經是史丹福大學的博士。人家一流大學可以拿翻譯成果去取代部分學術論文,因為翻譯也要做研究,特別是古典的東西。
我在投稿的文章裡主張,我們應該看重翻譯,國立編譯館應該做些事。當年少不更事口出狂言。回到臺大後,我鼓勵學生用翻譯作品替代部分論文,論文字數可以少一點。寫碩士論文當然是很好的學術訓練,可是譯作可以真正對社會有所貢獻。那時候規定好像論文要八十頁,我建議可以減半到四十頁,另外附一個至少是中篇小說(Novella)份量的譯本。這個提議在系裡奮鬥了很久,終於通過了,可是研究生很少選這條路,因為翻譯已經很累了,還要寫四十頁論文,相較之下把四十頁論文變成八十頁並不那麼難。現在國外也還是一樣,做一個經典的翻譯,花的工夫比寫博士論文還多,翻譯作品就像是寫博士論文,難道不能得一個學位?所以基本上大家的觀念裡,翻譯依然是次等的(secondary)。
賀荃(Linda Hutcheon)在《改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裡說,改編雖然出現在原作之後(second),但它不是次等的,而是可以跟原作鼎足而立。這又牽涉到臺灣社會忽略人文、藝術、文學的現象,幾十年來未見改善。另外,還有就是市場的問題,你那本《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經典譯注版賣了有沒有一千本?
單德興
大概有。最近我才聽說,突然間大陸那邊要跟聯經訂幾百本的經典譯注版,所以他們正在趕印。但是有時候半年才賣個幾本,境遇很難講。
彭鏡禧
對。光是以臺灣的市場來講,愈來愈差。少子化姑且不說,就是不肯讀書嘛。何況現在有Kindle電子書閱讀器就可以看了。我也不知道該不該憂心紙本書的市場,因為還是有幾家出版社願意出書。我不是憂心自己,是憂心書店會不會虧本倒閉。
|翻譯與信仰
單德興
你曾提到 “measure for measure” 典出《聖經》。我留意到,你翻譯的簡體字版《暴風雨》(The Tempest)譯後記結尾特別提到,一般人認為那個劇本是大和解的結局,其實未必。你提到《聖經》告訴我們,寬恕非常難,需要七十個七次,從結尾主角博思波(Prospero)的用詞可以發覺他並沒有完全放下。我好奇的是,你的信仰、你對宗教的詮釋,與你的翻譯有沒有關聯?
彭鏡禧
其實沒有。莎士比亞受基督教影響,研究這方面的人很多,不是新的學問。我讀《聖經》,特別是《新約》,覺得這是很好的人生哲學,是人生路上很好的指引。《聖經》上講,人心詭詐是你猜不透的。《量‧度》(Measure for Measure)的主題是莎士比亞愛講的題目,表面與現實(appearance and reality)並不一致,往往表面是一套,內心是另一套。在戲裡,代理公爵的人本身很好,如果沒有碰到試探,一輩子都會是一個很好、嚴謹的人。但是當試探來了,有些人就容易跌倒。另外,他做出了這些事,別人該怎麼饒恕他?如果依法究辦,那就把他處死;你判人家死刑,我也判你死刑,這就是 Measure for Measure,意思是用同樣的方式,或是 quid pro quo,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惡有惡報……總之各種譯名都有它的道理。所以能不能原諒這樣一個人?戲裡別人問被冒犯的修女,你要不要原諒這個人?旁邊那個真正的公爵就說,不可能,如果你原諒了他,你弟弟的鬼魂會來抓你。旁人一直告訴修女不可以原諒,但她還是選擇原諒,那就是出自真心的諒解,而不是像博思波的表面和解。我覺得讀莎士比亞跟讀其他文學作品一樣,都使人更瞭解自己,更瞭解這個世界,心胸變得更寬大,懂得與人為善。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會擴大你的境界、你的心胸,所以我不太理解「文人相輕」。
單德興
一般研究你的翻譯時,基本上都是留意你的文學翻譯,尤其是莎士比亞。但我留意到你也翻譯了《荒漠甘泉》,而且閱讀這本書讓你決定接臺大戲劇系的系主任。我想問的是:第一,你翻譯宗教文本的因緣?第二,翻譯宗教文本跟文學文本有沒有什麼不同的體驗?
彭鏡禧
這裡面有點小誤會需要說清楚。二○○○年我在芝加哥訪學期間,每天跟燕生讀一篇《荒漠甘泉》。這個牽引是很奇妙的。我回到臺灣後,臺大外文系畢業的兒子信之開始翻譯工作,工作項目之一就是重新翻譯《荒漠甘泉》。這本書是他翻譯的,當然也不光是他一個人翻譯,前面有人翻了一部分,他接手繼續完成。《荒漠甘泉》中譯已經存在多年,版本很多,但都不是全譯本,特別是每篇後半部引用的詩常常刪去。於是出版公司打算出一個全譯本,信之就做了,做完以後,想請爸爸看一下,所以你看到那個封面上是「彭鏡禧審訂」。
這本書每篇通常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簡短的《聖經》引文,第二部分是作者自己靈修的心得和感悟,第三部分是作者引用的詩歌,有長有短,但不是每篇都有第三部分。我把每篇引用的詩歌都重新仔細看過,該修正的錯誤修正,該押韻的地方押韻,把它弄成詩該有的樣子,這是我做的部分。這些詩是靈修的作品,跟我們平常接觸的英詩不一樣,可是詩的寫作技巧一樣,我就用同樣的標準來修改。
單德興
過程中有沒有因為處理的是宗教文本,而有比較不同的體驗?我之所以會這麼問,是因為有一次我在校訂自己翻譯的聖嚴法師著作時,有幾天覺得特別安詳,這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後來也沒再出現。也就是說,宗教文本作為靈修文本,它的影響可能會反映在精神上。
彭鏡禧
這我不記得了,但常常閱讀的東西都會影響到你,那或許是潛移默化之功,譬如《哈姆雷》肯定對我有些影響。天天閱讀其實也是靈修的一部分,對我們的靈是有幫助的。
單德興
剛剛你提到閱讀文學作品會讓人更瞭解自己,心胸更寬大,也更能與人為善。對你個人來講,文學與宗教,或者說,文學與終極關懷的關係如何?
彭鏡禧
終極關懷跟宗教有點關係。我相信有上帝,相信信徒最後會回到天家,自然不會恐懼人生的終點。一個人如果能夠做到今天突然去世(drop dead)也無遺憾,我覺得是最好的境界。有人到最後掙扎得很厲害,那是比較痛苦的。如果有人說他隨時都準備好了,基本上是因為他有一個信仰,這是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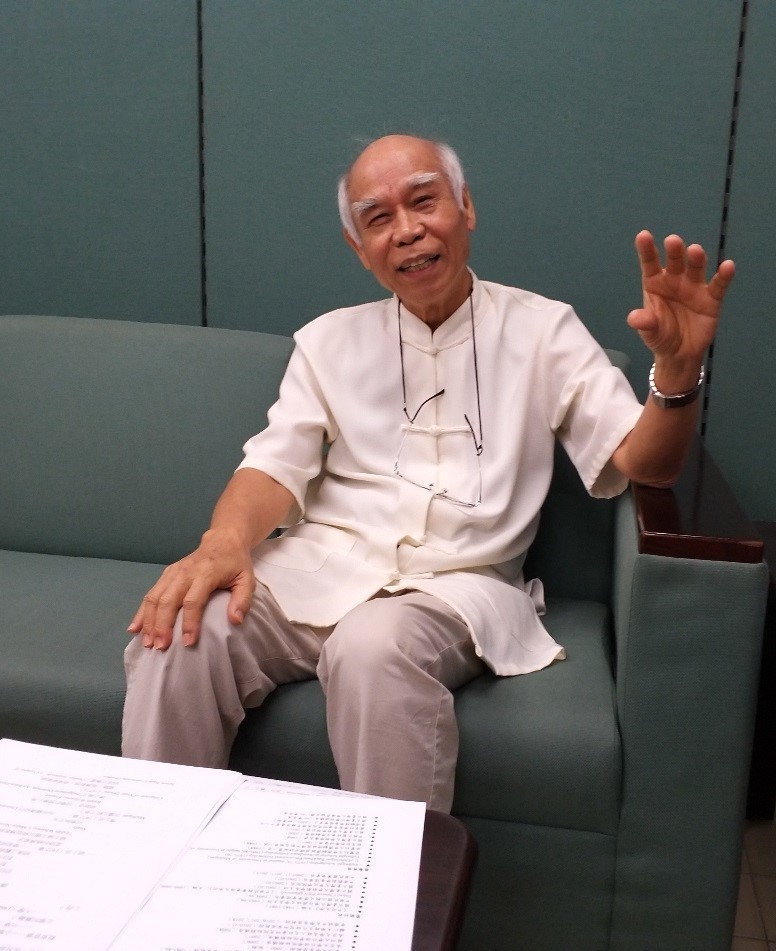
|自我評價與未來計畫
單德興
訪談的結尾,想請你談談對於自己不同角色的評價,像是自己作為學者、老師的評價。
彭鏡禧
我想是中上吧,B+。至於作為老師,我覺得可以拿A-,因為我覺得自己當老師當得還不錯,學生跟我保持很好的關係,也會不時彼此關心。我自己受惠於很多好老師,希望自己也能做個好老師。多年前一位學生送我一塊牌子,我到哪裡教書都會帶著這塊牌子放在桌面,上面寫著: “He who loves teaching helps others love learning.” (「老師熱愛教,有助學生熱愛學」。)我盡量讓學生學得愉快,培養學生的自信。若有學生告訴你,「老師,你這樣講可能是錯的」,我覺得這就成功了。
單德興
對於自己身為學者,為什麼那麼自謙?
彭鏡禧
不是謙虛。其實我的成果不是那麼多,其中有不少是翻譯,就把自己貶下來了,也許勉強是 B+到A-之間。
單德興
你的譯作有很多讀者,改編成戲劇後來看的人也很多,這些翻譯的影響其實比論文更大。
彭鏡禧
……而且我覺得比較重要,但是對學院裡的其他人來說,可能不這麼覺得。是不是優秀的學者或許有客觀的標準,譬如我雖然在臺大有些著作得獎,28 但是在國科會(科技部)從來沒得過傑出研究獎,傑出是A的話,優良就是B+。
單德興
但是傑出獎得主未必能像你這樣膺選為臺大傑出校友。
彭鏡禧
這是不同的主客觀標準,而且應該是多方面的累積。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一通電話來告知說你得獎了。我自己做過推薦委員,知道誰被誰推薦是不能洩露的。當然很高興有人認可你的努力。
作為基督徒,我最多是B。本來作為基督徒要傳福音,譬如我碰到單德興,我希望你接受福音。基本的概念是接受福音就有得到永生的機會,你真正愛一個人就應該這樣做,把福音傳給更多的人,但我沒有做到。
單德興
你用身教,未必要言教。
彭鏡禧
我覺得我真的是做得不夠。作為一個譯者,我可以給自己A-。
單德興
太謙虛了吧。
彭鏡禧
至少在這一塊,我是很專心在做。就像我講的,翻譯莎士比亞的時候,覺得自己以前接受的所有有形、無形的訓練,就是為著這個時刻。
作為一個人,更不能說了,B。全部的自我評價就是這樣,不是因為你訪問我,我特別謙虛。這些題目我會先想想,什麼樣是A、A+,設立一個標準,再去衡量自己。作為一個人,有沒有犯過錯?犯了無數個過。你對人真的有你設想得那麼好?還是其實沒那麼好,有很多自私、甚至不堪的念頭?B 就是不在社會上鬧事。
單德興
這比一般世俗的標準高很多。
彭鏡禧
也不能這麼說。《聖經》上寫耶穌到某個地方,有人抓了一個女人過來,因為她犯了姦淫罪,要遭到投石。群眾要看耶穌怎麼處裡。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就可以拿石頭砸她。結果從老到小一個個離開,因為每個人都犯過錯,沒有人是清白完美的。所以要幫作為一個人的自己打分數,應該看你是不是一個善良的人,我覺得我也許70%是善良的,那就是還有30%的不足。是不是高標準?可以說是應該的標準。
單德興
你現在已經是從心所欲之年。回顧自己的人生跟學術生涯,有沒有一些不同的階段?有些什麼感想?
彭鏡禧
人的際遇多半不可掌控,但我們可以決定如何樣利用這些際遇。我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我的家境在一般人看來是很普通的、中下的。父親是公務員,養了一大群小孩。客家人本來就很重視教育,特別是從鄉下出來的。我大哥也很重視教育,他覺得教育是改變生活的唯一方法,他自己是學理工的,可是他替家裡訂了《國語日報》,所以我們家所有小孩的國語文都不錯。我弟弟彭鏡毅還會唱京戲,粉墨登場,中文非常好,書林書店的蘇正隆先生可以證明。
除了父母兄長的支持,每個階段我都有過很好的老師;不好的老師應該也有,但很少在我記憶裡出現。剛進小學時,陳照明老師,進了亂哄哄的教室就指著我說,你做班長。這種機會不是每個人都有。四年級的陳彰龍老師暑假在家替同學們補習,我沒錢繳補習費,老師跟我說不用繳。初中、高中、大學都有很好的老師。到美國也是,除了柯潤璞,還有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魏大可。這些人對我的影響很大。一九八一年的在耶魯大學那年,有一次英文系開了很大的演講會,紀念作家喬依斯(James Joyce)逝世四十週年。除了學生以外,還有退休的老教授跟他們的配偶都來聽學術演講,令人感動。他們的談吐高雅,還有整個環境裡培養出來的一種重視文學的態度。另外一個記憶也是在耶魯,英文系裡一位老師出版新書,系裡同仁開了個小派對恭喜他。我們臺大外文系裡有人出書,同事們都不知道。我覺得應該有個互相扶持的氣氛,互相鼓勵,彼此瞭解。
單德興
你未來有哪些計畫?
彭鏡禧
我希望能夠繼續教書,不教書也要持續看書和翻譯,除此之外,我不太會做其他的事。到目前我出版了七本莎劇翻譯,第八本《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已經翻完了,這是經典譯注計畫的最後一個,書稿已經交給科技部結案,但還要修訂,也需要寫一篇緒論,全書審查後才能出版。這是先要完成的計畫。
單德興
那個譯本根據的是Arden版,還是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版本?
彭鏡禧
根據Arden版。這齣戲的版本問題不大,不像《哈姆雷》和《李爾王》。選用Arden 版,主要是它的參考資料詳細。我也參考其他學術版本。我前兩天剛碰到呂柏伸,他問我什麼時候把《仲夏夜之夢》翻出來。這也是當初我列的計畫之一。他想要用我的翻譯去導這齣戲,我說,看看吧。我希望有時間可以多做點翻譯。另外就是教書,現在很簡單,只教詩的翻譯、詮釋問題,或是跟莎士比亞相關的課程。這些題目我做起來有興趣,而且不用另起爐灶。這些是我大概想做的事。
單德興
我經常在訪談結尾會詢問受訪者對於訪談的看法。你討論過莎劇的獨白(soliloquy),把它分為四類。我的問題可能有點修辭上的矛盾(oxymoronic)或弔詭(paradoxical):訪談主要是受訪者表達他的看法,如果以獨白的角度來看,你會如何把訪談視為獨白?它的性質和作用如何?
彭鏡禧
受訪者也需要自我打岔或者別人打岔,不要變成自言自語(monologue),因此訪問者(interviewer)變成一個提詞者(prompter)。你這個想法很好。你送我的訪談集《卻顧所來徑》,後來我帶到學校給博士生看。因為之前我把呂柏伸導的《皆大歡喜》演出版DVD給他們拿回去看,也給他們看了劇本,然後討論。我叫他們每星期寫一篇文章寄給我,其中一個博士生在文章裡提到一個問題:要怎麼做訪談?我就跟他們說,你們看看單老師這本書,就可以知道訪談者要做什麼預備工作。訪談有很多種,記者訪談、雜誌社訪談、學者訪談、深入訪談等等。單老師說他的靈感來自於《巴黎評論》(Paris Review)。我說,當你要做有深度、有意義的訪談,第一件要做的就是知道受訪者平常怎麼想,去讀受訪者的作品,至少要讀特別有意義、有影響的幾本。必須要瞭解受訪對象,就好比你要寫一篇讀書報告,自然必須把那本書讀得很好,現在受訪者就是這本書,你要讀這個人,挖掘疑問與有興趣的地方,訪談時才會有有意義的交流/對話(meaningful dialogue)。
單德興
我受中山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張錦忠之邀,寫了一本《訪談的技藝》的小書,裡面談到受訪者與訪問者之間的互動,並且把訪談者的角色分為幾類,也包括了提詞者。書中也提到訪談就是一期一會,利用這個獨特的機會,挖掘出愈多東西愈好。
彭鏡禧
謝謝你。
1.張系國的〈孔子之死〉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刊於《大學新聞》。
2.Williams, Oscar (ed.) (1984) The Po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from Walt Whitman to Dylan Thoma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中國人迻譯西洋文學,歷史已經很悠久了。卽是在臺灣的近二十年,也翻譯了不少作品。但是,成果仍然不能令人滿意:一方面固然是量不多有些質不好,另一方面便是缺乏有組織有計畫的成套翻譯。我希望《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全部出版後,在西洋現代戲劇這個區域裡,一位中國讀者不會有想讀而無書可讀的遺憾。」參顏元叔(1973)〈關於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布雷希特戲劇選集:四川好人》(臺北:驚聲),頁2。
5.《淡江評論》創刊於一九七○年,《中外文學》創刊於一九七二年。
6.彭鏡禧(1973)《布雷希特戲劇選集:四川好人》、《布雷希特戲劇選集:高加索灰闌記》,共兩冊(臺北:驚聲)。
7.Ching-Hsi Perng (1978) "Reappraising Edith Wharton." American Studies 8.1: 81-118.
8.第一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淡水會文館舉行,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在中國」(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9.Ching-Hsi Perng (1977) "Judgment Deferred: An Intra-Genre Criticism of Yüan Dram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0.Hayden, George A. (1971) "The Courtroom Plays of the Yüan and Early Ming Period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no.34: 192-220; Hayden, George A. (1971) "The Judge Pao Plays of the Yüan Dynasty" (〈元代包公戲〉),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1.Ching-Hsi Perng (1978) Double Jeopardy: A Critique of Seven Yüan Courtroom Drama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2.入選密西根大學出版的亞洲學術著作共計一百本。該計畫現已完成,可至網站fulcrum.org/michigan自由閱讀、免費下載、或訂購紙本。
13.《拾穗》為臺灣戒嚴時期以翻譯為主的綜合性月刊,一九五○年五月創刊,一九八九年四月停刊。彭鏡禧曾以「彭敬兮」等筆名在該刊發表短篇小說及劇本翻譯,如〈富蘭克林與痛風夫人的對白〉(Benjamin Franklin, "Dialogue Between Franklin and the Gout")、〈一枚胸針〉(Isaac Bashevis Singer, "The Brooch")、〈人間喜劇:回想一九六八那年頭〉(Goodman Ace, "The Human Comedy: Way Back in '68")等。
14.張思婷(2016)〈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與政治:以《拾穗》為研究對象〉。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論文。
15.Barrett, William [白瑞德] (1969)《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彭鏡禧譯(臺北:志文出版)。
16.Gide, Andre [紀德] (1971)《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彭鏡禧譯(臺北:志文出版)。
17.Cohen, Hennig [柯恩](編)、朱立民等(譯)(1971)《美國劃時代作品評論集》(Landmarks in American Writing)(臺北:新亞);彭鏡禧譯了四篇:〈艾德格.愛倫.坡的《怪譚奇聞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霍桑的《七角大厦》(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惠特曼的《我自之歌》(Song of Myself)〉、〈亨利.詹姆士的《奉使記》(The Ambassadors)〉。
18.彭鏡禧(2001)〈一九六九年版譯序〉。紀德(著)《非理性的人》(臺北:立緒),頁18。
19.葉新雲(2001)〈二○○一年版代序:存在哲學不是非理性的〉。紀德(著)《非理性的人》(臺北:立緒),頁7-13;彭鏡禧也為這版本寫了〈二○○一年版修訂版前言〉(參頁15-16)。
20.胡耀恆(1971)〈歐美的現代戲劇潮流:兼評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上、下),《中國時報》,1971年3月12日至13日,第10版。
21.彭鏡禧(譯)(1973)《終局》,收於《貝克特戲劇選集》(臺北:驚聲);《布雷希特戲劇選集:四川好人、高加索灰欄記》,兩冊(臺北:驚聲),後者修訂為《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與鄭芳雄合譯;臺北:聯經,2005)。《白納德之屋》收於《羅卡戲劇選集》(臺北:驚聲,1970)。《西方男兒》收於《辛約翰戲劇選集》(臺北:驚聲,1970)。
22.彭鏡禧(1997; 2009)〈戲劇效果與譯文的字序:《哈姆雷》的幾個例子〉。《摸象:文學翻譯評論集》(臺北:書林),頁163-183。
23.彭鏡禧、夏燕生(譯)(1989; 2007)《好詩大家讀:英美短詩五十首賞析》(臺北:書林)。
24.彭鏡禧(1997; 2009)《摸象:文學翻譯評論集》(臺北:書林)。
25.彭鏡禧(2009)〈恰如其分: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翻譯類散文組優勝作品討論(附原文與第一名譯作)〉。《摸象》,第二版(臺北:書林),頁203-209。
26.辜正坤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於一九九八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繁體版可參閱《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臺北:書林,2006)。
27.彭鏡禧(2019)〈跨文化作品的「原創」本質〉。《文訊》no.410: 171-173,該文並作為代序,收於陳芳(2019),《莎戲曲與跨文化劇場》(臺北:臺灣師大出版社),頁i-v。
28.James Fenton (2012) The Orphan of Zhao (London: Faber and Faber)。原定二○二○年六月於上海首演的原創音樂劇《趙氏孤兒》,係改編自芬頓同名劇本,金聖華、彭鏡禧翻譯,徐俊導演、金培達作曲、梁芒作詞。現因新冠病毒,預訂延到二〇二一年五月上演。
29.〈苦心孤譯《哈姆雷》〉獲二○○六年國立臺灣大學優良論文獎;《細說莎士比亞:論文集》獲二○○六年國立臺灣大學傑出學術專書獎;《威尼斯商人》譯注獲二○○七年國立臺灣大學傑出學術專書獎等。
──────────
彭鏡禧,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及外國語文學系名譽教授教授、輔仁大學講座教授。致力於莎士比亞研究、文學翻譯近 5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