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土著的迷思》的當代意義
◎李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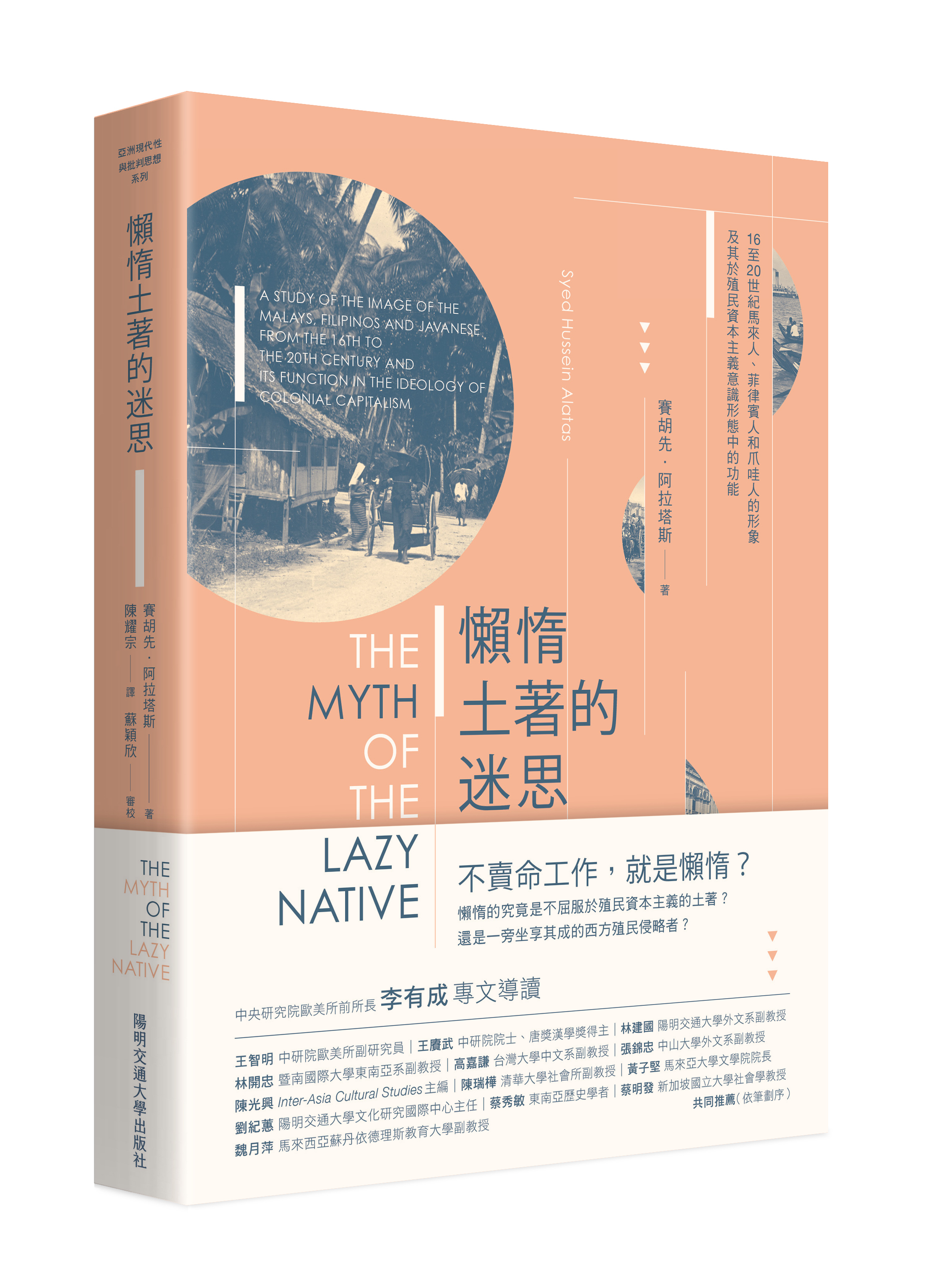
《懶惰土著的迷思》(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書影
|一
我初窺後殖民理論當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最早讀到的相關著作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薩依德的扛鼎之作初刊於一九七八年,第一版的封面即十九世紀法國著名畫家傑宏姆(Jean-Léon Gérôme)充滿東方情調的作品〈弄蛇者〉("The Snake Charmer")。在我一九八八年的論文〈重讀《拉奧孔》〉中,[1] 我即曾借用薩依德在《東方主義》書中有關想像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的概念,闡釋雷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如何為文學與繪畫劃定疆界,並且在以文學為中心的霸權支配下,繪畫如何「一再遭到壓抑、殖民、邊陲化的命運」。[2] 一九九三年薩依德出版其《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就在他這本皇皇巨著中,我初次注意到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的著作《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這本書出版於一九七七年,比《東方主義》還早一年。作者阿拉塔斯這個名字似曾相識,後來我才想起,他曾經是一位在我年輕的歲月中短暫出現的政治人物。他還是一位馬來學者,出生於印尼,其時任教於新加坡大學馬來研究學系,並兼該系系主任一職。新加坡大學為今日新加坡國立大學前身,一九七○年代末期南洋大學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一九八○年被迫走入歷史,並被併入新近易名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懶惰土著的迷思》有個冗長的副書名,概括說明此書旨在研究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與爪哇人的形象,以及此形象在殖民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的功能。
副書名中有兩個用辭對全書的主題與論證至關緊要:「意識形態」與「殖民資本主義」。就意識形態而言,阿拉塔斯開宗明義指出,殖民者「利用懶惰土著觀來合理化殖民地勞動力動員過程中的強制與不當行為。……為土著及其社會塑造出一個負面形象,藉此正當化與合理化歐洲人對其他地區的征服與支配」。[3] 換言之,在阿拉塔斯的觀念中,「懶惰土著」雖然只是個標籤,但卻也是殖民主合理化與合法化其宰制被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根源。阿拉塔斯的話一點不假,一九一一年,牛津大學教授弗列徹(C. R. L. Fletcher)與英國著名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們合著的《英國史》(A History of England)一書中,就是抱持著這樣的殖民心態的。他們表示,澳洲「只有一些甚至連弓箭都使不上手的可悲的黑人」;而在非洲,「每個地方的土著無不歡迎我們的治理帶給他們的恩惠與正義」;他們還認為,西印度群島上的土著「懶惰、邪惡,除非迫不得已,他們缺少認真改進或工作的能力。在這樣的氣候裏,幾根香蕉就足以養活一個黑人,他幹嘛要更努力工作?」[4] 由此可見「懶惰土著」的成見是如何深植人心,根深蒂固。吉卜林一八九七年(一八九九年修訂)的長詩〈白種男人的負擔:美利堅合眾國與菲律賓群島〉("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正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用今天的話說,這首詩毫不掩飾地展現其無所不在的白人至上論,白人責無旁貸,必須對土著擔負起其教化任務(civilizing mission)。[5] 當然,誰都看得出來,這是一首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張目的詩,這樣的認知意識自然也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感情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難得會受到時人的挑戰。
再就殖民資本主義而言,阿拉塔斯在梳理了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與韋伯(Max Weber)等對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的說法後,特別強調東南亞與歐洲的歷史進程是如何截然不同。在他們看來,東南亞並未完全複製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模式,當然更未經歷類似的發展階段。最明顯的是,十九世紀時「金融與工業資本主義在歐洲社會內部所產生的作用,並未同樣產生於東南亞社會」。[6] 簡單言之,依阿拉塔斯的說法,此時的東南亞早已成為歐洲各國的禁臠,列寧(Vladimir I. Lenin)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導致帝國競逐的壟斷資本主義,已在東南亞運作」。[7] 這種具有帝國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是「西方強權在殖民地遂行統治的總體意識形態」,[8] 阿拉塔斯即將之統稱為殖民資本主義。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原著出版於一九一六年,他在這本為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定調的書中特別提到霍布森(J. A. Hobson)與其《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一書。[8] 我最早對帝國主義的了解其實也是來自霍布森這本出版於一九○二年的著作。早在這一年前,在位六十三年的維多利亞女皇去世,漫長的維多利亞時代終告結束,其子愛德華七世繼位。霍布森原為《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即今日的《衛報》——派駐南非的記者,其主要任務在採訪波爾戰爭(the Boer War)。從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二年,大英帝國的軍隊在此戰爭中遭遇波爾人的頑強抵抗,雙方死傷慘重,最後以簽訂弗里尼欽和約(The Vereeniging Treaty)結束。波爾戰爭使大英帝國的海外聲勢首次受到重挫。霍布森為費邊社(the Fabian Society)的成員,之前也曾著書立說,研究資本主義與當代社會問題。他顯然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只是他的社會主義主要源於英國本土的激進政治傳統。他的《帝國主義研究》以很大的篇幅探討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主要在彰顯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依附關係。這層關係可以推前到工業革命的興起。簡單地說,由於機器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供需失調,為了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帝國必須對外擴張,尋找新的消費市場,以滿足資本家的慾望;同理,為了支援資本主義的生產,必須自海外大量進口原料,帝國更需要擴大版圖,開發與奪取更多的資源,對外殖民於是成為最為方便的捷徑,殖民主義就是帝國強權實踐其佔人土地,奪人資源的意識形態基礎。[9] 阿拉塔斯在其《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中只有一處提到霍布森,不過他並未對霍布森的說法多加析論,事實上他所說的殖民資本主義在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一書中不難找到理論與實踐上的助力。
阿拉塔斯在其書中對列寧也是一筆帶過,即上面提到的有關壟斷資本主義的說法。列寧在思構與撰寫其《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時其實頗受霍布森的啟發。他曾在一九○四年翻譯了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而且很有系統地認真研究帝國主義的議題。在《列寧全集》第三十九卷《關於帝國主義的筆記》中即收集了他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間的閱讀箚記和心得,有關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的筆記就佔了三十五頁。[10]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裏,列寧大量徵引霍布森的材料和觀點,讚揚他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儘管他對霍布森嘗試為資本主義尋找出路的做法不盡同意。在列寧看來,帝國主義不過代表了資本主義社會最後的垂死掙扎,資本主義不得不仰賴帝國主義進行海外剝削,正好說明了其早已來日無多。

《懶惰土著的迷思》(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書影
我援引霍布森與列寧的觀點無非想說明,阿拉塔斯所說的殖民資本主義基本上不出霍布森與列寧的論點,可能是出於學科的考慮,或者其他我們無法臆測的原因,他無意在論證的過程中多方指涉霍布森與列寧。阿拉塔斯在其書〈導論〉的第一句話,就自承其方法屬於知識社會學,而且他還進一步強調,「在西方發展而成的現代社會科學的普遍與抽象概念,不應自動套用於非西方社會」。[11] 這話言之成理,對非西方世界的學術社群應該有棒喝之用。誠然,許多概念乃至於理論的形成是有其社會背景與文化的獨特性的,目的在解釋或解決原生社會與文化所面對的問題。因此在援用這些概念或理論時,確實有必要作適度的調整與協商。此之所以阿拉塔斯會說,「建構新概念供研究東南亞社會之用,是符合真正的社會科學方法應用的」。[12] 顯然在他看來,殖民資本主義正是他所說的新概念,因為此概念隱含的意識形態「試圖透過其所聲稱的目的,即現代化與文明化臣服於西方強權的社會,來合理化西方的統治」。[13] 這個用心值得肯定,而且是任何接受西方現代學術訓練的人在面對自身社會與文化時無法迴避的問題。有趣的是,儘管阿拉塔斯取徑於知識社會學,在方法上與霍布森和列寧的政治經濟學大相徑庭,只是他所標舉的殖民資本主義卻與霍布森和列寧的看法不謀而合。他說:「工業革命之所以對殖民地產生影響,原因在於這些殖民地除了是原料和經濟作物的生產地,也是工業產品的銷售地。」[14] 具體地說,當時歐洲與其殖民地在產業形態和經濟活動方面還是有根本的差異的:「殖民地的主要資本主義投資是在礦業和種植園業,不在商業和工業;在殖民地展開的工業活動無論範圍或層次皆微不足道。所以……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並沒有促進現代科學與技術的傳播,因為它沒有與工業結合,也因為採礦和種植無需多少科學與技術,就能初步生產那些供直接輸往歐洲的原料。由於原料的加工是在歐洲進行,殖民地並沒有從那些與加工相結合的科學與技術實踐中受惠。」[15] 由於這些差異,影響所及,「工業革命透過科學與工藝所帶給歐洲社會的體制與結構轉型,並沒有發生在殖民地社會」。[16] 工業革命為歐洲原有的階級、行業及體制帶來巨變,可是這一切並未發生在歐洲各國的殖民地,相反地,「那些無助於殖民資本主義運作的體制、行業和階級若不是被消滅,就是被棄置而停滯不前」。[17]
|二
阿拉塔斯在其書名中既已清楚指出,所謂「懶惰土著」是個迷思(神話),因此他的意思是,這個形象是想像的,是建構的,缺少現實的基礎。他的計畫顯然是在解構這個形象,為這個形象除魅,或者將之去迷思化。在阿拉塔斯撰寫其《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時,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早已是獨立國家,殖民主也已離去多年,他筆下的馬來人、爪哇人及菲律賓人當然更是獨立國家的主人。——之前殖民者心目中的土著是否「懶惰」,不論就理論或事實而言,事過境遷,應該已不重要。《懶惰土著的迷思》原本就是一本具有後殖民意識的著作,歷史地回顧與批判殖民主義的來龍去脈,並檢視殖民統治賴以存在與延續的前因後果。殖民統治原來就是一個複雜的心理過程,這個過程對被殖民者——阿拉塔斯心目中的土著——所造成的傷害是多方面的,資源的掠奪、物質的剝削,乃至於自由的限制只是有形的惡果而已,精神的挫折、心靈的扭曲及心理的創傷才是被殖民者難以去除的疤痕。法農(Frantz Fanon)許多有關殖民心理學的著作——諸如《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垂死的殖民主義》(A Dying Colonialism)、《大地哀鴻》(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等——處理的多的是這些問題。他在《大地哀鴻》一書中就這麼指出,「殖民主義不會滿足於僅僅控制某個種族,或者掏空土著一切形式的心智而已。出於某種不正常的邏輯,殖民主義轉向被壓迫人民的過去,將這個過去扭曲,破壞,摧毀」。[18] 法農的意思是,殖民主總會想方設法,處心積慮地貶抑與否定被殖民者的歷史與文化,希望經過長期潛移默化,讓被殖民者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漸漸失去信心,這是教化任務極為重要的議程與環節,同時也是殖民主遂行與鞏固其殖民宰制的重要技術。這也說明了何以在殖民主離去之後,被殖民者所蒙受的傷害未必就會立即形消於無,此之所以後殖民並不等同於去殖民,美化殖民統治,甚至懷念或崇拜前殖民宗主國者大有人在,現實中這種例子不少,最常見的如歌頌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讚揚殖民主如何闢建鐵路,規劃都市建設,辦理教育,開發農田水利,改善公共衛生,甚至創建典章制度等,殊不知殖民主這一切作為的目的無非為了便於有效治理,為了確保其長期殖民統治,賡續其對殖民地的剝削與掠奪。更甚的是,有的人在對殖民主感恩戴德之餘,竟故意忽略殖民過程中被殖民者遭受的暴虐殺戮。法農的觀察至今仍然不失其批判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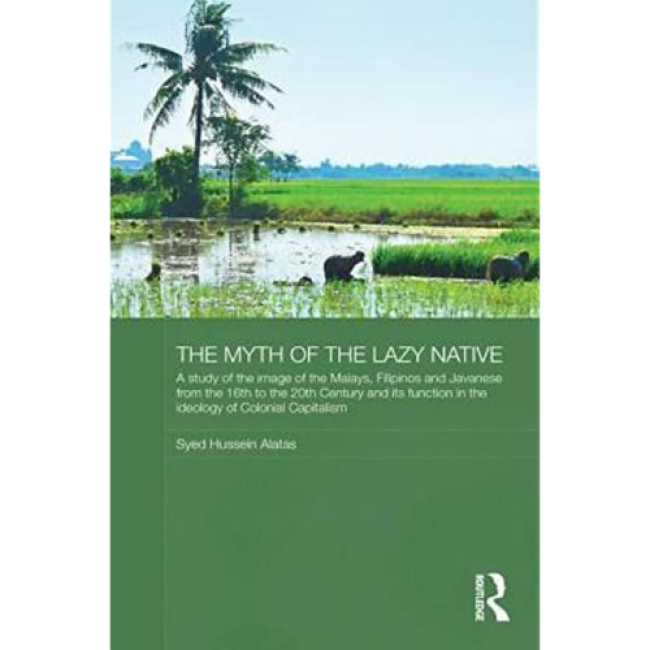
英文版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書影
因此消解「懶惰土著」這個迷思是去殖民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被殖民者重建其自我形象,找回其民族自信與自尊必經的一道關卡。用後殖民論述的話說,這是一種反否定(counter negation)的行為,其用意在否定殖民主對被殖民者的惡意否定。殖民主義原本就是一套怪異和蠻橫的論述,在殖民主看似理性的論述背後,其實潛藏著諸多非理性的成分。「懶惰土著」的意識形態只是一例,其目的不過在刻意將土著刻版印象化(stereotyping),這在歧視思想與行為中屬於相當常見的形式,是經由高度總體化與概括化的過程,泯滅個別差異,模糊個人的獨特面貌,納入固定分類,並代之以定型,是強化種族偏見的結果。[19] 上文提到弗列徹與吉卜林對澳洲、非洲及西印度群島各地土著的描述,無不是殖民時代廣被接受的對土著的刻板印象。其實阿拉塔斯也有類似的體認,他在《懶惰土著的迷思》的〈導論〉中就這樣直指問題的核心:「在人類歷史上,對其他群體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屢見不鮮。我們必須把這些刻板印象和偏見中的普遍成分和特殊成分區分開來,才能對現象有較深入的認識。」[20] 這也正是《懶惰土著的迷思》全書最根本的關懷,書中的主要章節無不在努力消除這些偏見與刻板印象,撥開籠罩著土著形象的迷霧,以見出土著在歷史與現實世界中的真實面貌。
問題是,這種偏見與刻板印象流傳日久,積非成是,竟至深入人心,迷思也就因此廣被視為真實,甚至到了後殖民時代,土著早已當家做主,這樣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依然牢不可破。這正是《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作者最大的恐懼。阿拉塔斯是一位馬來學者,他特意以馬來人的遭遇為討論的實例,正好透露了他內心真正的憂慮。對他而言,他的論述計畫處理的不只是學術問題,亦且是現實世界中必須面對,必須解決的問題。他在〈導論〉中這樣坦然表示:
對馬來西亞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則歷史研究習題: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迫切需要被糾正,因為這個形象依然在部分有影響力的非馬來人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也影響了部分馬來知識分子。此形象只要繼續存在,就會損害民族融合的努力。這個形象也導致馬來人在就業上一定程度的歧視:一些僱主避免聘用馬來人,因為他們認為馬來人懶惰。許多人也認為,馬來人天生不具經商能力。這一切觀念都是源自於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21]
〈導論〉中的這段文字至關緊要。在我看來,這段文字其實隱含《懶惰土著的迷思》全書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s),阿拉塔斯或許無意,這段文字卻意外地讓馬來人成為問題——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問題。《懶惰土著的迷思》除〈導論〉與〈結論〉外,全書共分十二章,專論馬來人的章節明顯佔大多數;即使其他章節,尤其涉及歷史部分,阿拉塔斯的論述對象往往也是更大的馬來世界,也就是一般統稱的「努山達拉」(Nusantara)。[22] 他的論述策略與節奏相當清楚,歷史批判只是必要的手段與過程,窮根究底無非在釐清問題的歷史根源,他更重要的議程無疑是當下現實中馬來人的問題。
就歷史問題而論,在全書的第一與第二章,阿拉塔斯就特別針對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包括葡萄牙人、荷蘭人與英國人等——對馬來人的觀察紀錄細加梳理。可想而知,他著墨最多的還是幾位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關係較為密切的英國人。譬如,第一章約有一半的篇幅討論的就是新加坡的開埠者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阿拉塔斯視萊佛士為馬來人民族性研究「重要的先驅」,他直接引述萊佛士的話說明其研究範圍:「我必須把馬來人視為一個民族,儘管他們分佈極廣,散居於蘇祿海與南大洋之間,東西以蘇門答臘和巴布亞或新幾內亞西部為界的所有海國,但他們都說同一種語言,並且保留著他們的性格特質與習俗。」[23] 換句話說,萊佛士所關注的對象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努山達拉」。據他的觀察,馬來人在遇到英國人之前,其民族性早已無可避免「處於衰敗狀態」,除了外部如宗教與外國人——阿拉伯人、荷蘭人及華人——的影響外,內部影響如土邦、酋長、縣長、村長等各方面勢力的傾軋,再加上缺乏使社會順利運轉的基本法制,整個馬來民族只能走向頹敗。萊佛士甚至認為,「說馬來人懶惰至極,只要他們還有一口飯吃就沒有人能夠說服他去工作,是相當正確的看法」。[24]
接下來的第二章,阿拉塔斯討論的對象則是兩位英國海峽殖民地的重要官員: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 1850-1946)與克利福(Hugh Clifford, 1866-1941)。瑞天咸於一九○一年至一九○四年擔任第十五任海峽殖民地總督。他留下幾本與馬來人有關的著作。阿拉塔斯在瑞天咸的《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一書中看到他對馬來人這樣的描述:「每個階層馬來人的首要特徵是不喜歡工作。」[25] 瑞天咸當然也設法為自己的觀察提出解說。一方面他發現,「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存在著十分巨大的鴻溝」,[26] 馬來人變得被動,只願意依統治者的命令做事。另一個原因則應該歸咎於馬來人所生活的地理環境。「一個人十二個月當中只需斷斷續續工作不超過一個月,用一個魚簍在河裏或沼澤裏撈魚,傍晚時分花一個小時撒網,就能獲得足夠的糧食。稍微努力一些,他就會有剩餘的東西可以販賣。這一點,加上這裏的氣候會讓人體趨於休憩放鬆,讓人腦陷入如夢似幻狀態而不事艱苦持久的勞作,也許足以說明馬來人與生俱來的怠惰。」[27]
有趣的是,與瑞天咸差不多同時代的克利福也有類似的看法。克利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間出任第十九任海峽殖民地總督,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馬來半島的東海岸度過的,由於他熟諳馬來語,因而與當地馬來人頗多交往。他也是作家,其長短篇小說與散文多以馬來亞經驗為素材。克利福是認真肯定英國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的,阿拉塔斯引述他所著《在宮廷與甘榜》(In Court and Kampung)一書裏的話說,面對馬來人,英國人的責任是「把我們認為最終會為這個族群帶來好處的實質上與觀念上的革命引進來」。[28] 他認為適宜馬來人生存的環境是中世紀,如果硬要他們接受十九世紀的文明,「他們自然就會趨於精神萎靡、無精打采,並且喪失原本健全的自尊了」。[29] 至於馬來人的勞動態度,克利福的看法也頗為消極與負面:「如果可以不工作,他們就絕不工作,而且通常不會因為受到極優渥薪資的驅使或誘惑,而勉強自己去工作。」[30]
對阿拉塔斯而言,不論萊佛士、瑞天咸或克利福,都是他在書的第九章所說的「業餘從事學術研究的行政官員」或者「業餘殖民學者」,[31] 他批評他們對馬來人的描述往往以偏概全,失之偏頗,正如十九世紀著名馬來文人文西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 1797-1854)引馬來諺語所說的,「一隻水牛沾了泥巴,整群水牛都被弄髒。」發生在馬來人身上的事,同樣也可能發生在英國人或歐洲人身上。阿拉塔斯特別提到文西阿都拉的《阿都拉傳》(Hikayat Abdullah)。他指出,文西阿都拉在他的自傳中強調,懶惰現象可能只是病態社會制度——如馬來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的一部分,不能視為常態,「並不是整個馬來社群的特徵。……馬來人的伊斯蘭價值觀是譴責懶惰和不公行為的。」[32] 阿拉塔斯進一步引述若干馬來人伊斯蘭教領袖的說法,證明「勤勞和努力工作是符合馬來人的價值觀的」,而且在伊斯蘭教的進步觀念中,「就包含了對懶惰行為的譴責」。[33]
|三
嚴格地說,阿拉塔斯對殖民者的批判只是其論述計畫的一部分,他更大的關懷是當下馬來西亞部分馬來菁英對相關議題的反應,他認為這些菁英「在殖民意識的影響下對自己社群的勤勞抱持懷疑的態度」。[34] 殖民者早已離去,其政治上的影響力也已不再。馬來菁英則不一樣。他們的態度可以左右政策的制定,影響社會生活,甚至決定國家未來的走向。具體呈現現代馬來菁英的態度的是一九七○年代初幾乎同時出版的兩本著作:一是由當時馬來西亞執政聯盟主要成員黨巫人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UMNO)出版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與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所著的《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在《懶惰土著的迷思》第九章結束時,阿拉塔斯不假辭色,直指核心,這樣批評這兩本著作:「這兩本書都是殖民意識形態的產物。它們是對殖民論述的一種回應,但它們所表達的回應和態度,顯然受到了殖民論述的制約。在這兩部作品中,閒散、不愛勞動、慵懶的馬來人形象十分突出。」[35] 換言之,這兩本出自現代馬來菁英階級的著作無疑坐實了兩百年來西方殖民者為馬來人所描摹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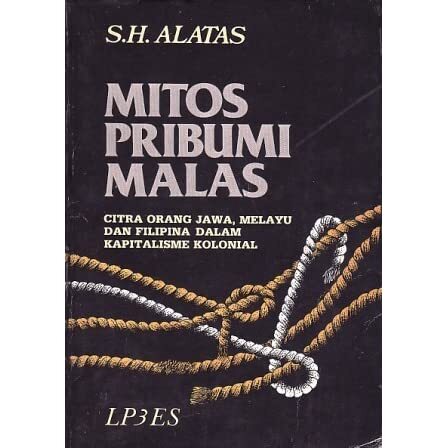
印尼文版 Mitos Peribumi Malas 書影
這兩本書出版時馬來西亞剛剛經歷了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種族暴動。這個被稱為五一三事件的歷史悲劇死傷慘重,事件之後政府當然提出了官方說法,只是民間的臆測與分析版本更多,真相如何至今仍然莫衷一是。[36] 總之,五一三事件毫無疑問是現代馬來西亞政治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事件發生之後,政府隨即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凍結憲法,停止國會運作,同時成立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暫時取代內閣,由副首相敦阿都拉薩(Tun Abdul Razak)領導,形同架空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的權力,而且通過一個個的行政命令取代過去的政策。有論者謂這是某種形式的政變,就權力結構的改變而言,其實不無道理。東姑阿都拉曼眼看權力旁落,大勢已去,就在一九七一年二月辭去首相一職,由敦阿都拉薩接任。國會復會後,同年政府開始施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逐步落實憲法規範馬來人特殊地位的第一五三條文。馬來菁英則將此所謂特殊地位解釋為馬來人應享的特權,而最能夠體現這些特權的就是令少數民族垢病與痛心的固打制(「固打」應音譯自英文"quota",配額之意)。執政的巫統在一九七一年推出《精神革命》一書顯非偶然,其目的自然是要為新的權力結構敲鑼打鼓,為日後馬來人優先或馬來人至上(Ketuanan Malayu)的政策鋪路。
《精神革命》是一本十四位作者的合集,由當時巫統的秘書長瑟努阿都拉曼(Senu bin Abdul Rahman)擔任主編。阿拉塔斯毫不掩飾他對這本文集的厭惡,他痛斥這是一本「由毫無深度的合理常識和絕對荒謬的推論混雜而成的書,……是最天真、最低智、定義最不明確的資本主義之作」。[37] 他指出,殖民資本主義對這本書「影響十分強烈」,而且「迴避了馬來人懶惰的問題」,至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曖昧,但肯定是傾向於視馬來人為懶惰的民族。」[38] 阿拉塔斯尤其在意書中對馬來民族的自貶自抑,在他看來,這種做法無異於內化乃至於延續殖民者長期灌輸的懶惰土著的意識形態。用他的話說,「《精神革命》對馬來人更加徹底的貶低,並非意味著一個新的馬來人形象的崛起。馬來西亞現有的統治階級與殖民主的連結並沒有斷裂。……他們仍然是在殖民主義思想範疇中運作。」[39] 我在上文曾經提到,後殖民未必等同於去殖民,阿拉塔斯此處對馬來人統治階級的撻伐是個證明。簡單言之,從阿拉塔斯對《精神革命》一書的批評不難看出,這本書完全體現了他在《懶惰土著的迷思》書中大力抨擊的兩項罪狀:懶惰土著的意識形態與殖民資本主義。
除此之外,阿拉塔斯認為《精神革命》一書只「提到了華人移民對國家財富增長的貢獻,卻沒有提到馬來人的貢獻」,他對此深表不滿。他的說法相當有趣。以下是他對《精神革命》上述說法的回應:
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馬來人。為警察部隊提供人力的是馬來人。國家主要的糧食生產者,尤其是在殖民時期,是馬來人。……馬來人對法治的貢獻也很可觀。……法治無疑對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馬來統治者與行政人員的支持,單靠人數不多的英殖民官員是不可能實現法治的。在管理井然有序的政府方面,馬來人的無數貢獻完全被忽略了。事實上,馬來人為創造一個讓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環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40]
阿拉塔斯的說法值得玩味。在他的認知裏,馬來人的重要貢獻,不論是殖民時期或是國家獨立之後,是扮演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的壓迫性國家機器。尤其在殖民時期,馬來人的貢獻無異於支持與協助殖民統治,就後殖民的視角而言,這是與殖民主的合謀共計(complicity),非但鞏固了殖民統治,甚至可能拖延了國家獨立的時間。這樣的貢獻其實是不值得誇誇其談的。阿拉塔斯不應該忘了,《懶惰土著的迷思》的構想是在批判殖民主義,他所稱頌的馬來人對殖民統治的貢獻與他的論述立場無論如何是扞格不入的。至於馬來人對糧食的貢獻,阿拉塔斯沒有提到的是,鄉村農耕土地多為馬來人所有,其他族群即使有意在糧食方面有所貢獻其實也力不從心的。
阿拉塔斯最後分析《精神革命》一書之所以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繼續貶抑馬來人的三個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巫統某些黨員確實體認到「馬來人處境糟糕」,並將此歸咎於馬來人的民族性;第二、相對於其他族群,獨立後馬來人的處境並未獲得改善,巫統有意藉貶抑馬來人的民族性逃避責任;第三、巫統希望藉此「合理化改善馬來人總體經濟狀況的具體計畫」。[41] 在我看來,阿拉塔斯的分析合情合理,只不過在這三個原因之中,第三個才是重點。《精神革命》或許如阿拉塔斯所言,是一本問題重重的著作,但此書所部署的論述策略相當清楚,毫不含糊;《精神革命》其實是一本有節奏,有方向,意圖明確的著作,其目的顯然在為新經濟政策辯護,而新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正是阿拉塔斯所說的「改善馬來人總體經濟狀況的具體計畫」。新經濟政策當然旨在落實憲法一五三條有關馬來人地位的精神,而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將這種精神付諸實踐的就是無所不在的的固打制:在行政、軍警、教育、經濟等領域,固打制像幽靈那樣,盤據在馬來西亞的現實中,其後果是,五十年來,馬來西亞始終深陷於種族政治的泥淖中,近百分之四十的華裔與印度裔公民不但公民權利受損,甚至淪為二等公民,馬來西亞也因此成為南非之後,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以種族界定人民生活的國家,其衝擊遍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而且越陷越深,至今無法自拔。種族政治激發族群矛盾,製造社會不公,影響所及,二○一八年十一月,在馬來統治菁英的抵制與威脅之下,馬來西亞政府甚至拒絕簽署具有普世價值的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42] 一個政權若只是為了一族之私,少了消弭歧視、申張公義、追求平等的理想、決心與意志,如何能建立一個進步、悲憫、文明的國家呢?
一九七○年馬哈迪出版其《馬來人的困境》一書,此時距五一三事件還沒幾個月,馬哈迪也因為反對東姑阿都拉曼而被逐出巫統,《馬來人的困境》更被內政部列為禁書,要到一九八一年馬哈迪擔任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之後才解禁。阿拉塔斯在撰寫《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時,馬哈迪已經重返巫統,甚至出任巫統中央執行理事會委員,並自一九七四年在吉打州其選區當選國會議員後,即先後擔任內閣教育部長、貿易與工商部長及副首相,早已成為權力結構的重要部分。在阿拉塔斯的轉述中,《馬來人的困境》是一本充滿陳見與偏見的書,馬哈迪的論述背後具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相信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法則,而且在態度上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頗多肯定。因此阿拉塔斯批評馬哈迪:「他對馬來人的種種看法受到了殖民資本主義的支配。」他認為馬哈迪的「精神世界並沒有與殖民思想完全決裂」。馬哈迪甚至這樣讚揚英國殖民主的治理成效:「獨立前,英國人把這個國家治理得很好。他們或許沒有給予非英國公民最好的待遇,但他們無疑是卓越的行政人員。他們的工作卓有成效。他們建立了高效率的公務員體系和充分發揮效力的執法機關。……他們建設公路和鐵路,徵收的稅款直接進入國庫並用於公共服務。」[43]
馬哈迪描述與論證馬來人的困境,在策略上每每以華人(偶爾提到印度人)為對比,在有意無意間似乎想要證明馬來人的困境與華人密切相關。譬如,阿拉塔斯指出,馬哈迪論證華人之優越性是如何出於歷史因素,因為數千年來,華人的祖先總是天災人禍不斷,戰亂與饑荒幾成常態,所以對華人而言,「生活就是一場持續不斷的生存鬥爭」,[44] 無法適應者只能遭到無情淘汰。馬來人的歷史經驗則大不相同。馬來半島有大量的平地與河岸,阿拉塔斯轉述馬哈迪的話說,每個馬來人「都有大量的土地可用,從來不需要為了耕種或定居而去開墾山林。富饒的熱帶平原和豐富的糧食來源」,在這種情形下,歷史上中國人經歷的苦難,馬來人是無法想像的。在馬來半島,即使是「最弱和最懶惰的人,也能過得相對舒適」,甚至「結婚和繁衍後代」。[45]
說到婚嫁與繁衍後代,馬哈迪進一步表示,華人的習俗反對近親通婚,「與馬來人偏向近親繁殖的情況恰成對比」,[46] 因此華人能夠「繁衍出最好的血統和特性」。馬哈迪的結論是,「遺傳和環境影響使馬來人變得如此虛弱,以致在面對華人移民的衝擊時,他們無能為力,只能退縮。凡是馬來人能做的,華人都能做得更好,更便宜」。[47] 馬哈迪接下來的跳躍式推論更為可議,他把馬來人群居鄉村的現象歸罪於華人對城市土地的蠶食鯨吞。即連華人勤奮,華人肯學習馬來語也變成罪過,因為這樣華人會佔盡機會。馬來人的機會就被取代了。「首先被取代的是貿易和商業,接著是技術勞工,最後甚至是非技術勞工。居住地也被取代,因為馬來人不得不搬出城市。他們沒有理由留在城市裏,除非受僱於政府。事實上,由於城市地區土地價格上漲,加上各種稅費,他們被迫賣掉產業,轉而購買較便宜的鄉村地」。[48] 更甚的是,馬哈迪批評華人和印度人因為來自人口眾多的國家,行為不檢,不知禮貌,「在他們的生活中,總是與教養聯繫在一起的高貴情操完全闕如」。華人與印度人移民之所以能夠成功,馬哈迪認為,部分原因在於馬來人「禮貌和謙讓的心理」。[49] 他還因此提出相當煽動性的結論:「馬來人住在鄉村和處於貧困狀態,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這是種族特質衝突的結果。他們隨遇而安和寬容忍讓,華人則格外勤奮和精於商業。兩者一旦接觸,就會產生無法避免的結果。面對具掠奪性的華人的攻勢,馬來人就退居到比較差的地區。」[50]
從阿拉塔斯對《馬來人的困境》一書的引述與轉述不難看出,在馬哈迪的想像世界裏,他所謂的馬來人的困境主要肇因於外來移民——尤其是華人。在馬哈迪看來,刨根究底,當下馬來人的困境華人難辭其咎,自然得負起相當的責任。《馬來人的困境》表面上是一本自省的書,實則其整個論述反而是諉過他人居多。與《精神革命》的眾多作者一樣,馬哈迪整個論述計畫的出發點無非也是為憲法有關馬來人地位的規定張目。這一點早就被阿拉塔斯戳破。他一方面痛斥《馬來人的困境》書中「有許多與史實不符之處」,[51] 並且以不少篇幅在細節上質疑馬哈迪書中的許多舉例,認定「馬哈迪所談論的馬來人的負面特質若非誇大其詞,就是在判斷上有所偏差」;[52] 另一方面他也承認,「整體而言,這本書可說是為馬來人的憲法保障所作的論述詳盡的辯護」。[53] 換句話說,在馬哈迪的認知裏,馬來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對移民步步退讓,犧牲不少,他對馬來人的處境不論是自艾自憐,或者是憤怒指控,其用意不難揣測,特別在五一三種族暴動之後:憲法對馬來人地位的保障是協助馬來人走出困境的重要設計,不容其他族群置喙或挑戰。一九八一年,距《馬來人的困境》出版十一年後,馬哈迪終於得償夙願,在第三任首相胡先翁(Hussein Onn)辭職之後繼任大位,至二○○三年缷任,呼風喚雨二十二年。二○一八年在離職十五年後,他捲土重來,以九十二歲高齡再度拜相,成為第七任首相,儘管這次任期不到兩年。馬哈迪左右馬來西亞歷史進程數十年,馬來西亞國家發展的功過成敗,他要擔負很大的責任。他的執政理念,在《馬來人的困境》一書中早已形塑,一旦大權在握,當然要將理念付諸實踐,因此在他任內,固打制雷厲風行,尤其在教育領域,不少華裔與印度裔學子淪為犧牲者,成績優異卻被排拒在公立大學志願之外,種族不平等與社會分化日益嚴重。馬哈迪在工商企業方面刻意扶植馬來人,甚至還因此造成朋黨主義橫行,至今尾大不掉。
|四
過去四、五十年,東南亞乃至於整個亞太地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在地緣政治上,當英國與葡萄牙這兩個最後的殖民主分別結束其對香港(一九九七)與澳門(一九九九)的殖民統治之後,亞太地區完全進入後殖民時代,阿拉塔斯在《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中批判不遺餘力的殖民主義已經一去不返。只不過殖民主義留下的傷疤未必徹底消失,正如我在上文一再強調的,在現實情境中還不時可見殖民主義魅影幢幢,在關鍵的時刻仍會伺機現身還魂;何況新舊帝國從未忘情於眼前的地緣政治利益,因此我說後殖民時代不必然就會順理成章出現去殖民現象。在這樣的脈絡下,阿拉塔斯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儼然是個未竟的計畫,他在書中舉證歷歷,析論新的統治菁英如何內化殖民者的價值,如何複製土著的負面形象與殖民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時他在其書臨結束前還不忘這樣自省:他認為追溯土著形象的意識形態根源「不應被視為試圖建構一個相反的形象,即完美的土著形象。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土著社會都存在著許多缺陷,其中之一就是一個能有效發揮作用的知識社群」。[54] 阿拉塔斯並未進一步闡釋他所謂的知識社群,從他對《精神革命》與《馬來人的困境》二書的撻伐不難看出,這些統治菁英顯然未能構成他心目中的知識社群,他們既無能反省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傷害,反而在殖民遺緒中坐困愁城,走不出殖民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窼臼。這也正是薩依德在其《文化與帝國主義》中何以要對《懶惰土著的迷思》多方肯定的原因。他說:
在阿拉塔斯的《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中,最尖銳的抨擊之一是針對那些在自己的思想中複製殖民意識形態的馬來西亞人,這個意識形態製造並維繫「懶惰土著」的理念。在若干教人想起法農非難民族資產階級的段落中,阿拉塔斯指出殖民資本主義的遺緒如何殘留在新近獲得獨立自主的馬來人的思想中,將他們局限在「殖民資本主義的思想」的類別裏——換言之,他們在方法上並未自我意識到與發現到階級屬性對思想造成的影響。[55]
我引用薩依德上述的話旨在說明,阿拉塔斯四十五年前出版的《懶惰土著的迷思》至今仍具有其當代意義,尤其擺在當前馬來西亞的政治脈絡裏,書中探討的議題還不失其適切性。當阿拉塔斯著手撰寫《懶惰土著的迷思》時,政府剛完成其第二期大馬計畫(1971-1975),他對這個計畫的評價相當負面。究其原因,阿拉塔斯坦然指出,馬來人統治菁英「不會公開承認這主要是貪腐、裙帶關係、計畫執行不力和缺乏體制創新所致」。[56] 半個世紀過去了,阿拉塔斯當年所批評的種種現象非但尚在,甚且變本加厲,益形嚴重。憲法一五三條早為馬來人統治菁英所綁架,固打制已經形成慣例,上層階級的朋黨主義更是牢不可破。此外,政治倫理蕩然,利之所趨,政客跳槽成風,甚至因此被輿論譏為政治青蛙,政局混亂,政府失能,再加上當下新冠病毒疫情嚴峻,政府幾近束手無策,阿拉塔斯約五十年前批判的窘境究竟伊於胡底?
在這樣的背景下,三十年後我有機會重溫阿拉塔斯的經典,感觸尤其深刻。阿拉塔斯曾經短暫參政,不過他並未像多數馬來人那樣加入巫統或泛馬伊斯蘭教黨,一九六八年,他與林蒼佑、陳志勤、王賡武、威拉班(V. Veerappan)等成立馬來西亞民政運動黨(簡稱民政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其政綱之一即在要求檢討憲法一五三條有關馬來人特殊地位的規定。該黨在一九六九年的大選中頗有斬獲,不料大選後三天就發生五一三種族暴動,從此馬來西亞選擇走上一條由種族政治界定的狹隘而又崎嶇的歷史進程。一九七二年,林蒼佑等主張加入聯盟,組成新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阿拉塔斯、陳志勤、威拉班等反對與種族為基礎的政黨合作,選擇退黨並另組馬來西亞社會正義黨(Social Justice Party of Malaysia),希望能夠延續民政黨成立當初的理念。可惜知識分子參政,空有理想,結果功敗垂成,這個新的政黨就因一九七八年的大選失利,不少黨員易幟跳槽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而宣告解散。阿拉塔斯自一九六八年開始就任教於當時的新加坡大學,在結束了他短暫的政治生涯之後,他繼續以學術論政,對貪腐的問題著力最深。[57] 一九八八年他離開新加坡,回到吉隆坡,出長馬來亞大學,至一九九一年止;一九九五年之後轉任馬來西亞國民大學(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教授。《懶惰土著的迷思》出版於阿拉塔斯退出實際政治前夕,他自許其方法學得力於知識社會學,不過在我看來,他在書中的歷史敘述與分析更多受到歷史社會學的啟發。《懶惰土著的迷思》無疑是一部旅美肯亞作家兼學者恩古基(Ngũgĩ wa Thiong'o)稱之為「去除殖民心靈」(decolonizing the mind)的著作,[58] 具有深刻的進步與解放意義,阿拉塔斯藉歷史考察介入政治批判,他的重要指涉始終沒有脫離他所身處與關心的政治現實。這可能也是重讀《懶惰土著的迷思》最令我感動卻又不免心情沉重的原因。
——二○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深夜於臺北
*本文原為賽胡先‧阿拉塔斯著,陳耀宗譯,蘇穎欣審核《懶惰土著的迷思》(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一書的導論。
[1] 本文後來改題為〈《拉奧孔》的文學中心主義〉,收入李有成 (2006)《在理論的年代》(臺北:允晨文化),頁131-148。
[2] 李有成,《在理論的年代》,頁145。
[3] Syed Hussein Alatas (1977)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Frank Cass), 2;中文譯本見賽胡先‧阿拉塔斯 (2022)《懶惰土著的迷思: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陳耀宗譯(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頁44。
[4] C.L.R. Fletcher & Rudyard Kipling (1911) A History of Englan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292.
[5] Rudyard Kipling (1929) "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erse, Definitive Edi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6] Alatas 6;阿拉塔斯51。
[7] Alatas 6;阿拉塔斯51。
[8] Alatas 6;阿拉塔斯52。
[9] Vladimir Lenin (1989) [1939]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5.
[10] J.A. Hobson (1963) [1902] Imperialism: A Study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5-109.
[11] 列寧(1963)《列寧全集》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39卷,頁450-484。
[12] Alatas 1, 7; 阿拉塔斯52。
[13] Alatas 7;阿拉塔斯52。
[14] Alatas 7;阿拉塔斯52。
[15] Alatas 18;阿拉塔斯67。
[16] Alatas 19;阿拉塔斯69。
[17] Alatas 18;阿拉塔斯67。
[18] Alatas 18;阿拉塔斯67。
[19] Frantz Fanon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210.
[20] 李有成(2016)《記憶》(臺北:允晨文化),頁77。另請參考David Theo Goldberg (1993) Racist Culture: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25-126.
[21] Alatas 29;阿拉塔斯83。
[22] Alatas 16-17;阿拉塔斯65。
[23] 在修訂這篇論文時,剛巧看到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一則報導,印尼國會於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二)通過遷都法案,將於二〇二四年開始,在加里曼丹建立新的首都,以取代擁擠不堪且日見陸沉的耶加達,新首都已被命名為努山達拉(Nusantara)。
[24] Alatas 38;阿拉塔斯92。
[25] Alatas 39;阿拉塔斯93。
[26] Alatas 44;阿拉塔斯100。
[27] Alatas 45;阿拉塔斯102。
[28] Alatas 45;阿拉塔斯103。
[29] Alatas 46;阿拉塔斯103。
[30] Alatas 46;阿拉塔斯104。
[31] Alatas 47;阿拉塔斯105。
[32] Alatas 130;阿拉塔斯215。
[33] Alatas 138;阿拉塔斯231。
[34] Alatas 141;阿拉塔斯236。
[35] Alatas 142;阿拉塔斯236-237。
[36] Alatas 142;阿拉塔斯237。
[37] 像某些歷史事件一樣,五一三種族暴動至今真相難明,官方與民間各有說法。官方將事發原因歸咎於反對黨因大選後挑釁遊行造成的後果;民間則多視此為執政的巫統內部權力鬥爭的陰謀設計。歷史學者廖文輝甚至認為「這是場有計畫的政變」,當時以副首相敦阿都拉薩(Abdul Razak)為首的巫統少壯派刻意藉暴動逼迫開國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讓出政權。見廖文輝(2019)《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臺北:聯經),頁409-410。另請參考王國璋 (2018)《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39-41。有關五一三事件的英文著作請參考Kua Kia Soong (2007)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Petaling Jaya: Suaram Komunikasi); Leon Comber (2009) 13 May 1969: The Darkest Day in Malaysian History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有關五一三事件的口述歷史則請參考五一三事件口述歷史小組編 (2020),《在傷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個人口述敘事》(八打靈再也:文運企業)。另外,有關涉及五一三事件的文學作品研究,請參考李有成 (2021),《五一三的幽靈》,《思想》43期(2021年9月),頁329-353。這一期的《思想》即以「五一三的幽靈」為題,推出五一三事件五十週年紀念專號,收入多篇於「後五一三馬來西亞文學與文化表述國際會議」(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年5月13-14日)發表的論文。
[38] Alatas 149;阿拉塔斯242。
[39] Alatas 149;阿拉塔斯243。
[40] Alatas 154;阿拉塔斯249。
[41] Alatas 151;阿拉塔斯245。
[42] Alatas 154-155;阿拉塔斯249。
[43] 請參考林友順 (2018)〈大馬反種族歧視公約觸礁〉,《亞洲週刊》(2018年12月9日),頁15。
[44] Alatas 162;阿拉塔斯261。
[45] Alatas 155;阿拉塔斯250。
[46] Alatas 156;阿拉塔斯251。
[47] Alatas 155;阿拉塔斯250。
[48] Alatas 156;阿拉塔斯252。
[49] Alatas 158;阿拉塔斯254。
[50] Alatas 158;阿拉塔斯254。
[51] Alatas 161;阿拉塔斯260。
[52] Alatas 159;阿拉塔斯256。
[53] Alatas 174;阿拉塔斯276。
[54] Alatas 159;阿拉塔斯256。
[55] Alatas 238;阿拉塔斯358。
[56] Said, Edward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49.
[57] Alatas 181;阿拉塔斯285。
[58] 阿拉塔斯有關貪腐的著作甚多,請參考: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6); Corruption: Its Nature, Causes and Functions (Aldershot: Gower, 1990); Corruption and the Destiny of Asia (Petaling Jaya: Prentice Hall, 1999) 等。
[59] Ngũgĩ wa Thiong'o (1986)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r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