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隨筆:代序冼文光《巨人》
◎張錦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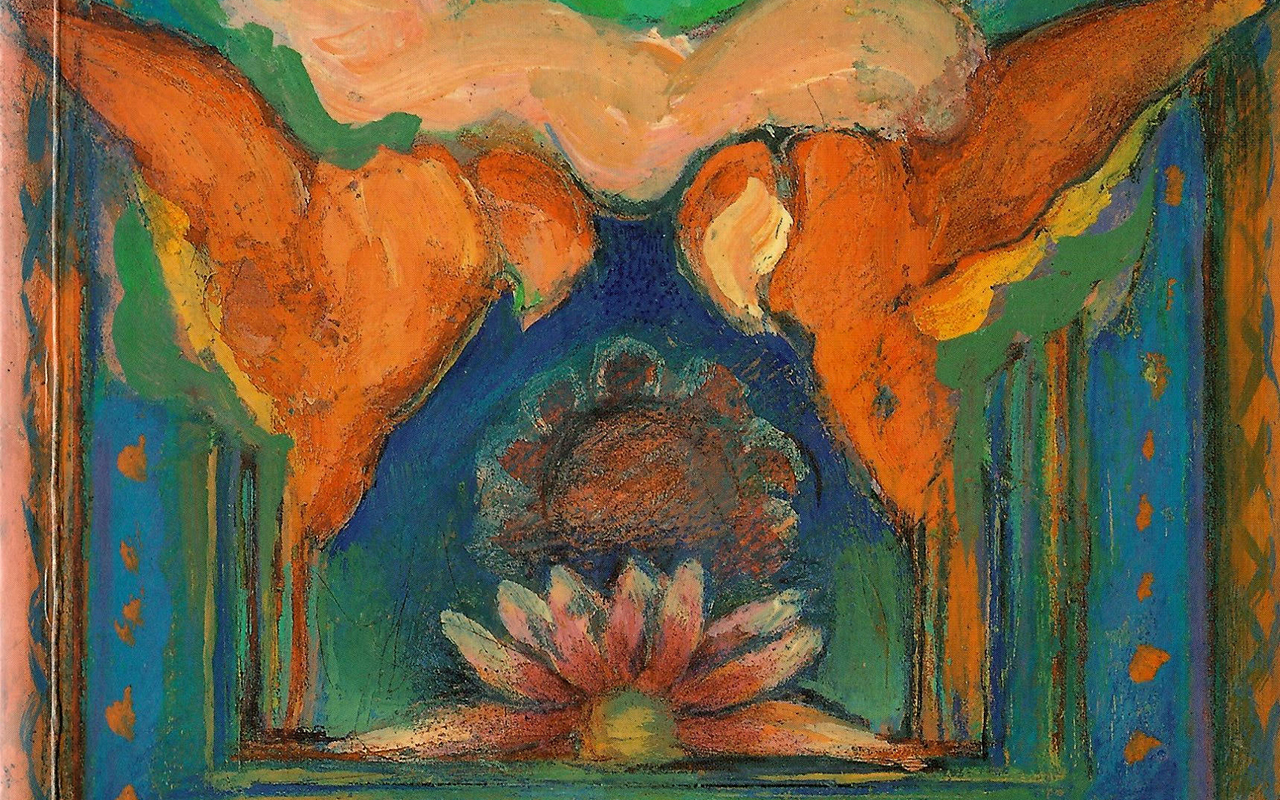
【二〇二二年六月九日】
冼文光「轉譯」陳瑞獻的《陳瑞獻詩集1964-1991》(智力出版社,1992)中十五首詩為「連環圖詩」。
「連環圖詩」(graphic poetry)借用的是graphic novel的概念。
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著名的具象詩或圖畫詩即graphic poetry。
當代日本留美女詩人藤本直子(Naoko Fujimoto)作圖畫詩就用graphic poetry一詞,那些文本有圖畫有英詩,當然也可叫「圖文詩」。
晚近盛行的graphic novel,多譯為「圖像小說」,或「圖文小說」,其實明清之「繡像小說」庶幾近之,但「繡像」一詞畢竟太古,且義近「插畫」,不如還是稱之為「連環圖」,即舊時「漫畫書」的另一說法。連環圖的漫畫不是單格,而是一格連一格,一頁接一頁,也可單冊或多冊,一冊接一冊,故曰連環。坊間流行的日本漫畫當然也是連環圖。
「連環圖詩」乃跨界的藝術。
字詞或聲音詩的連續空間裏一一前進,一行接一行,詩意在瞬間爆發,故詩為時間的藝術。
圖畫則是空間的藝術。視覺的進行,不是連續漸進,而是離心或向心,或離散,或遠或近,全幅展開,一覽無遺。
冼文光轉譯陳瑞獻詩,從翻譯的角度來看,屬於雅谷生(Roman Jakobson)所說的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不過現在看來,其實也是IP產業現象的一種——將陳瑞獻詩改編為「連環圖」或「圖像小說」,成為「文學轉譯」成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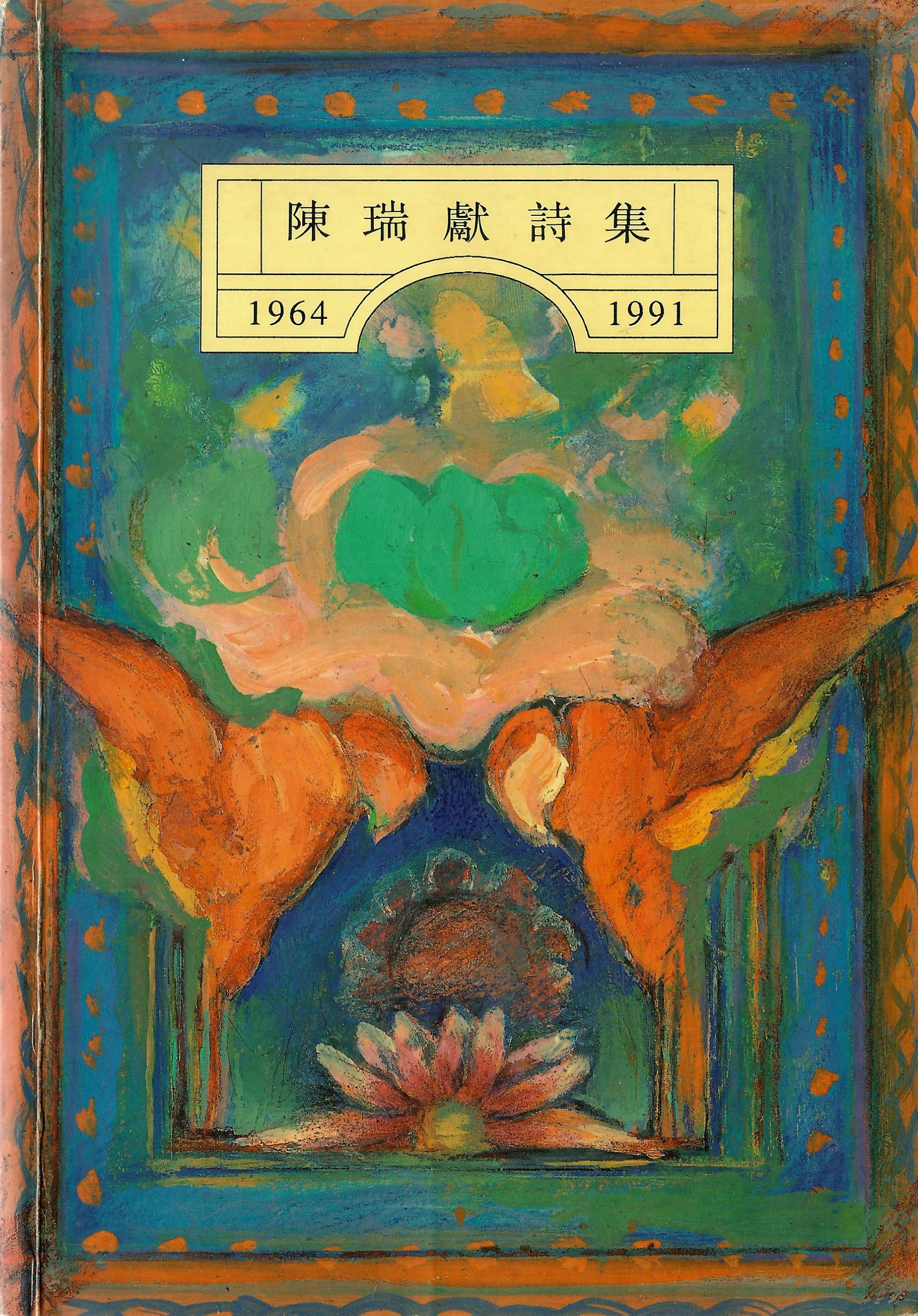
陳瑞獻詩集書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以下談談陳瑞獻詩〈一個詩人的房間〉及其圖像詮釋。
一個詩人的房間,房間的物,隨著字詞順序現形:一堆文件、一群壁虎、一隻雞、八隻八哥、眼鏡蛇、打字機、一隻野貓、一排鋁質蕃石榴葉、白眼圈巢、坐蓆、壁畫,辦公室。從特寫到全景,詩的空間逐漸擴大。詩十四行,可分十四鏡,也可從第十四行倒看,從全景到特寫。一如影片有框(frame),詩中有框:有窗、窗口、門、門楣、門檐、牆壁、房間⋯⋯。
冼文光翻譯或再創作的連環圖版〈一個詩人的房間〉是個多框文本(multi-framed text)。連環圖文本分割、分隔、分格,匡格,或全景,或中景,或特寫,皆在一覽之內,但框格之間充滿斷裂、縫隙、跳躍,屬於讀者的想像空間。
時間也是跳躍的。陳瑞獻的〈一個詩人的房間〉寫於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但〈一個詩人的房間〉也是陳瑞獻的一張素描,作於一九七七年底,畫中有窗,窗框竹製,室內有薔薇盆栽、小擺設,窗外有草地,有樹,有屋子,有雨簾的象徵。陳瑞獻將眾物放在一格畫面,透過窗,我們得以一覽窗室內外之物件與景象。
〈一個詩人的房間〉(1977)不是詩的插圖,而是詩的「前傳」——作為《蕉風月刊》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號的封面,我們最先看到的是「房間」,詩作〈一個詩人的房間〉(1981)中最後才出現的「一個詩人的辦公室」。但我們在這張作為封面設計的線條畫裏並沒有看到整個房間,也沒看到一堆文件、一群壁虎、一隻雞、八隻八哥、眼鏡蛇、打字機、一隻野貓、一排鋁質蕃石榴葉、白眼圈巢、坐蓆、壁畫。一詩一畫各有其有,各有其沒有。
詩與畫的〈一個詩人的房間〉的確都是一個詩人的房間:瑞獻於一九六八年進入法國駐新加坡大使館擔任新聞秘書。同年,已在文壇展露頭角的「詩人牧羚奴」創立五月出版社,出版開創新風格的現代詩集《巨人》,聚集六八世代新銳作者寫下星馬華文文學史新頁。「詩人牧羚奴」的辦公室,正是法駐新加坡大使館舊址。
詩中的「午睡」呢?過來午睡的「車伕」與「園丁」呢?其實,「午睡」不在瑞獻自己的封面畫,也不在文光的連環圖詩,而在瑞獻一九九七年的油彩畫作《未來詩人》裏:那是一個裸裎上半身側臥而睡的男子;那空間,也頓時成為一個(未來)詩人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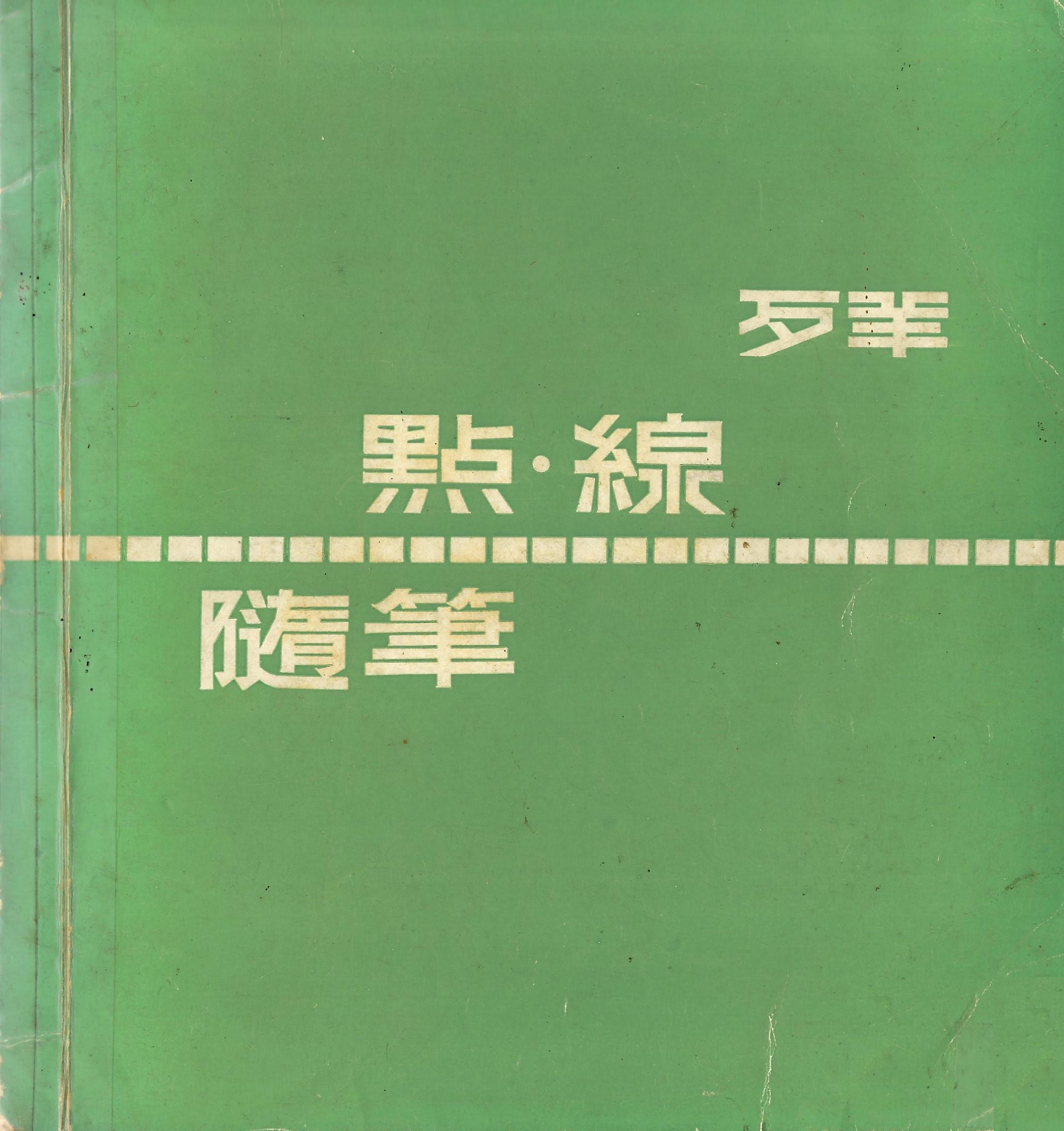
歹羊《點.線隨筆》書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冼文光寫詩寫小說之餘作連環圖,用剛強的粗獷線條來表現畫意,風格簡潔明朗,令人想起作卡夫卡〈變形記〉連環圖的辜勃(Peter Kuper),甚至機械主義的列哲(Fernand Léger)。歹羊的《點.線隨筆》有一則寫列哲,說他的畫面「一點都沒有抒情,有的卻是透露盡了現代工業文明所加壓於人類精神上的沉重氣息。」歹羊說列哲「沒有抒情」,大抵指的是這位法國立體派畫家作品構圖但見圓柱狀與管狀,畫中人物多立體幾何圖形。文光轉譯瑞獻詩為連環圖,彰顯其現代主義的元素,表現了小個體面對大都市文明的疏離與孤寂,及其內觀之旅,有敘事有抒情,發揮了連環圖文本的跨界特色。
——12 June 2022, Zuoy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