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討論「新南方」時我們在討論甚麼?——就「新南方寫作」訪問黄錦樹
◎訪談者|溫明明
◎受訪者|黃錦樹
◎訪談日期|May 17, 2023
◎編按|中國大陸《廣州文藝》雜誌九月號第578期的「新南方論壇」欄刊出廣州暨南大學溫明明教授對黃錦樹的線上訪問,然刊出時頗多刪節。這裏刊出完整版,被訪者云:「倘有需引用者,請依此版本」。
 (劉衍應攝影作品:〈皮影戲〉)
(劉衍應攝影作品:〈皮影戲〉)
溫明明
錦樹老師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應允接受此次網絡訪談。二〇一八年陳培浩在《文藝報》上發表文章〈新南方寫作的可能性:陳崇正的小說之旅〉首次提出「新南方寫作」的概念,此後經過楊慶祥等人的闡釋,已經成為近年來中國學界新的學術增長點,王德威等人也都介入到了這場討論中,不知您是否有注意到這一概念及其相關討論?
黄錦樹
我有在網上看到其中若干篇文章,但我想那不是我的戰場,也就沒太留意。
溫明明
我自己注意到這一概念,是因為在相關討論中,大部分學者將這一概念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從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一直延伸到東南亞各國,也就是說,「新南方寫作」已經溢出了中國文學的範疇,而將東南亞華文文學也囊括其中,在理論上對這一概念著力較多的楊慶祥甚至提出您是觸發他思考「新南方寫作」的第一個機緣。何以一群從事中國當代大陸文學批評的學者提出的概念會包含進東南亞華文文學?他們從東南亞華文文學這里發現了怎樣的「新南方」?站在「南洋」的位置,又該如何回應這個「新南方」?我們這次的訪談,我想大致圍繞「南洋」與「新南方」、東南亞華文文學與「新南方寫作」等關係來展開,並嘗試觸及以上問題。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南方」雖然是一個地理概念,但由於位置的不同,每個人心目中的「南方」都不一樣,您理解的「南方」和「新南方」是甚麼?傳統意義上的「南洋」是否在您思考的「新南方」或「南方」的地理空間內?
黄錦樹
我最開始、最直觀的感覺是——這如果不是個政治問題,就是個假議題。南北是相對的概念,端看你立足於何處。如果以南洋為立足點,整個中國都是北方。中國由於幅員廣大,南北間的山川地理氣候風土差異鉅大,因此自古以來不論政治、學術、思想、文學等都有南北異同論。但對我們原本就處在南方的人而言,實在看不出有甚麼談論「新南方」的必要(南方,是相對北方而言的;「新」南方,相對於「舊」南方而言),這顯然是北方視野的產物,和我們的存在關係不大。除非你渴望被納入那個體系,那就必須創造一個新的位置。楊慶祥的考量應該也是如此吧。為了安頓不屬於原來系統的,而嘗試創造一個新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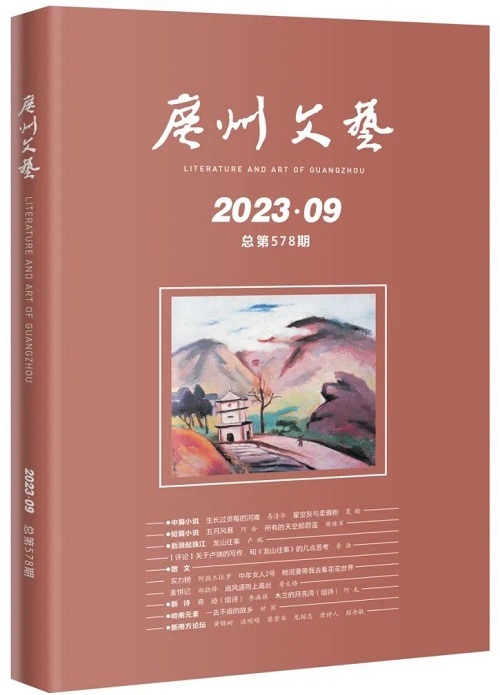
(《廣州文藝》九月號書影)
溫明明
南方不僅是一個自然地理,還應該是文學地理、文化地理和精神地理,這樣的話,我們在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對「南洋」的處理,就應該超越狹隘的空間主義視野,而應該把「南洋」作為風景、美學、文化乃至方法。您在自己的創作中是怎樣處理「南洋」的?在那茂盛的「膠林」和綿密的「雨」背後,有著怎樣的倫理寄托?
黄錦樹
審美理論層面上的南方,王德威的文章已做了相當全面的解說。寫作時不宜想太多,老張愛玲也說過,如果蜈蚣忙著數自己的腳,就走不了了。
溫明明
許多論者在討論「新南方寫作」時都談到了地方性寫作或文學的地理性,您能否從馬華文學的角度或結合自己的創作,談談您對文學中的「地方性」或「地理性」的理解?
黄錦樹
如前所述,大概是北方人從南方的某些文學作品中看到某些北方文學沒有的殊異性,想要給它們一個位置吧。從文學場域的角度看,那也是不錯的。大陸寫作的人太多也太競爭了,如果沒有新的位置,確實不好安頓。
至於我自己的「腳」,就不好多說了。
溫明明
「地方性」問題對馬華文學而言,並非新的話語,您認為有沒有所謂的「地方性知識」?如果有,對於馬華作家而言,「知識」的「地方性」體現在哪些地方,它又如何具備「地方性」?您是否認可馬華文學是一種「地方性」寫作?
黄錦樹
當然有「地方性知識」,除了極端美學自律的作品,文學和它的生產條件之間總是有著複雜多義的聯繫。我們多年來批評臺灣的馬華文學研究也多針對這一點,因為「地方性知識」殘缺,論述就難免隔靴搔癢。
馬華文學一直嘗試用地方性來界定自身(所謂的「南洋色彩」)。
馬華文學一直是一種地方性的寫作,但所有的世界性的作品都起源於地方,關鍵在於,能否既是地方的又超越地方。
在星馬,文學史上關於「地方性」論述資源也源自抗戰期間中國內地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南洋沒有中國那麼豐富的地方文化支援,幾乎就只剩風土、歷史和地方感性了。
溫明明
在我看來,「地方性」話語是需要警惕的,它會遮蔽掉很多東西,甚至使討論走向極端,包括將「地方性」和「世界性」二元化。您如何看待馬華文學的「世界性」及其文化主體性?
黄錦樹
馬華文學要進入中文文學的「世界體系」都很難了,還談甚麼「世界性」?馬華文學一直很難超越地方文學的格局,零星的個案超越了,可能就不被承認是「馬華文學」了。我那些大馬同鄉可是很重視「國籍」的。
溫明明
「新南方寫作」的倡導者有著明顯的「語言」關懷,他們試圖用「方言」來撬動正統「北方文學」的權力版圖,但「方言」及其書寫其實比較複雜。在「南方以南」的「兩廣」等地,方言是指北方通用語之外的其它語言,包括粵語、閩南語、客家語等,但到了「南方以南」的「南洋」,或許整體的「華語」都可稱之為「方言」/「少數語」,與之相關的寫作則成為了「方言文學」或「少數文學」。您如何理解東南亞華文文學創作中的方言?方言如何擺脫修辭,成為倫理或關懷的一種方法?
黄錦樹
我們和文學的遭遇首先是透過語言,你提到的兩廣福建都是白話文運動的棄兒,它和以北方官話為主體的白話文寫作是格格不入的;它的書面化本身就是個政治事件,甚至可說是個倫理事件。對某些人而言,那甚至可能是一種挑釁(可能會被視為帶著「分離主義」意味)。所有的方言寫作都是和標準語之間的妥協,差別僅在於妥協的程度。
張愛玲曾感慨「讀者三棄《海上花》」,屬「舊南方」的吳語書寫遭遇尚且如此,坦白說,我不覺得新南方「會有甚麼未來。自秦滅六國,書同文、車同軌以來,「中原」一直是偏好權力中心的標準語的。「舊南方」的蘇童好像就說過,江南人到了北方,就得學會把舌頭給捲起來。
「蓬勃的陌生」、「異樣的景觀」是在討論「新南方寫作」美學風格時常被使用的兩種說法,包括學者們在「新南方」視野下討論您和黎紫書的創作時,也很快就發現和指認了這種「陌生」和「異樣」,但實際上,任何一種「陌生」和「異樣」都必須建立在相對的參照系中,例如我讀您的《雨》其實並不感到陌生,但對於中國當代文學而言,這卻是「新」的。如果我們把「新南方寫作」理解為是對新的美學的召喚,您覺得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陌生」可能是甚麼?
黄錦樹
誠如你所言,陌生感是相對的。我讀張承志、曹乃謙、李銳、莫言、賈平凹等北方作家的作品,也常感到「蓬勃的陌生」、「異樣的景觀」。
邏輯上,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陌生性」對身在其中的我們而言必然是不可見的。
溫明明
討論「新南方寫作」其實不得不涉及它的兩個對立面:「北方」和「以江南為中心的舊南方」。但吊詭的是,由於位置的不同,嶺南、海南、粵港澳、南洋所面對的「北方」是不同的,「南洋」的「北方」甚至已經包含了「新南方」中的大部分版圖。您理解的「北方」是甚麼?東南亞華文文學要面對的「北方」又是甚麼?您如何看待這個「北方」?
黄錦樹
所以我說它可能是個假議題。
東南亞華文文學要面對的「北方」一直是中、臺、港,也即是我們的「上游」,資源的提供者,文學標準的制定者、評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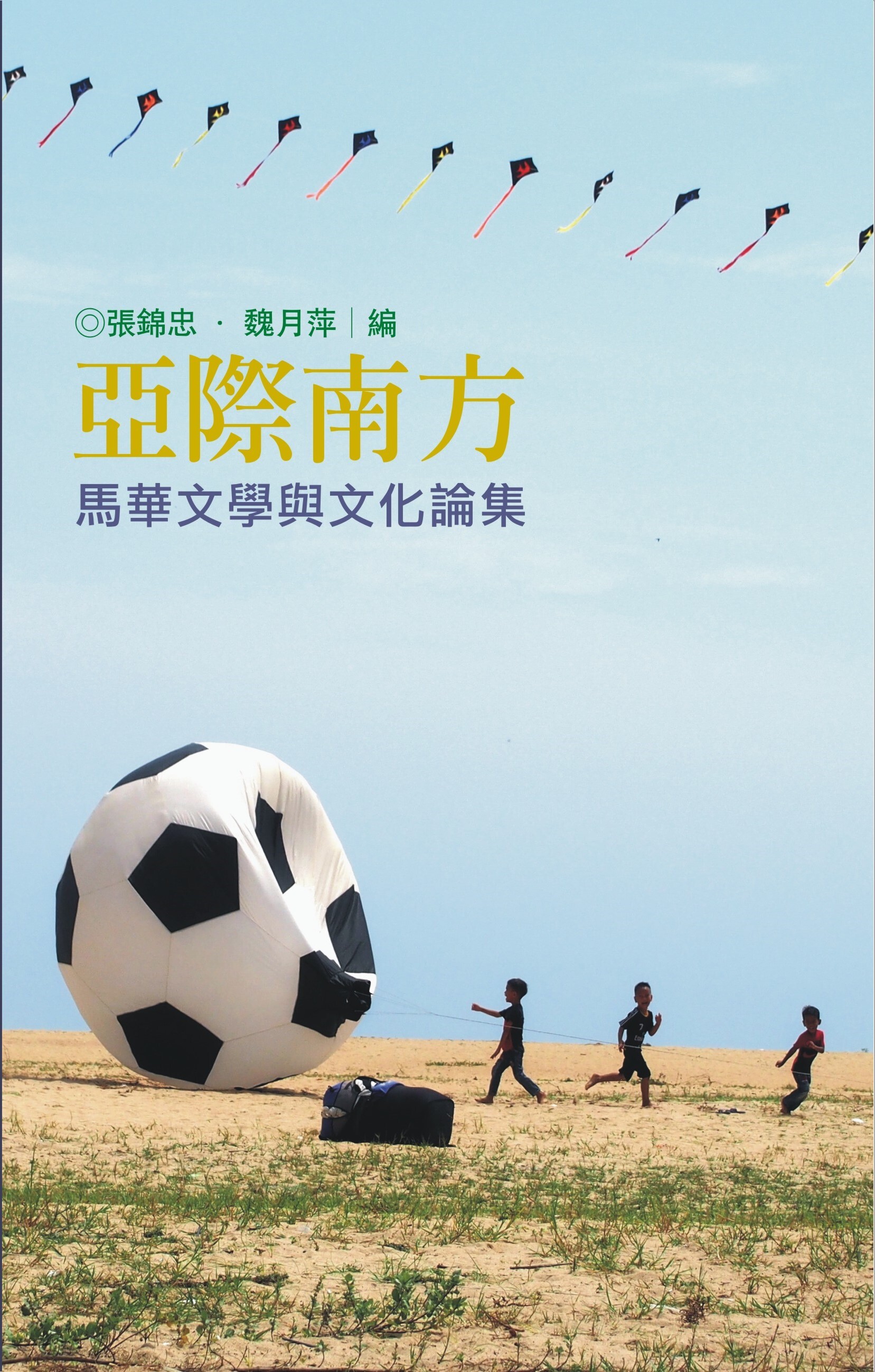
(張錦忠與魏月萍編《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封面)
溫明明
「新南方寫作」的倡導者有著強烈的解構意識,它試圖回應傳統的「北方文學/中原文學」及以江南為核心的「舊南方寫作」產生的諸多遮蔽,重新發現「中原」和「江南」之外的「南方以南」。就東南亞華文文學而言,如果「新南方寫作」也是具生產性的概念,那麽您認為「南洋」曾經遭受了怎樣的「遮蔽」?它需要解構的又是甚麼?
黄錦樹
「它試圖回應……重新發現」那是中國現代文學內部的問題了。
我論文也指出過,在當代中國文學的體制內,中國現代文學(1917-1949)和中國當代文學(1949迄今)是兩種不同的國家文學,前者是民國在大陸的國家文學,對人民共和國而言已完成且很短暫;後者還在迅猛的發展中,可能會延續數百年。港、臺、星馬的文學空間性和時間性則全然不同。
「新南方」真正的難題不是南洋,而是港臺。我每次到大陸開華文文學相關會議,提到臺港文學,大陸學者幾乎必然「炸毛」(借個貓打架的比喻),堅持它們是屬於中國的。臺、港這兩個南方幾十年的獨立發展的文學不是無意義的,它們的方言寫作的實驗也比兩廣福建海南成熟得多,但政治上對北方而言難免尷尬。譬如這個民國臺灣,它的文學可從一九四五往下推一直到今天。因此我會說,這個南方不止是地理問題,更是時間的、政治的問題,如果把它們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也許會造成結構性的震動。中原學者能接受一支歧出的、異質的、在英殖民體制、或受美援體制滋養長大的「淪陷區」現代中文文學,像楔子那樣深深嵌入共和國中國當代文學的血肉裏嗎?不面對名家輩出的臺港文學怎麼談新南方?
溫明明
討論到「北方」,必然要涉及到東南亞華人與神州的關系、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等等,您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論述和創作中實際上已經不斷在處理這些問題。「神州是海外華人的永恒欲望」、「死在南方」與「開往中國的慢船」等命題的提出都深具啟發性。尤其放在「新南方」的視野下,「死在南方」和「開往中國的慢船」甚至頗具反諷意味。您能否談談您對這方面的新思考?
黄錦樹
隨著中國崛起,這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我還在用小說的方式思考著,暫時沒甚麼可以奉告的。
溫明明
我在讀您的作品時,很早就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魯迅」味道,您在論述和創作中都曾處理過「魯迅」。對東南亞華文文學而言,「魯迅遺產」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命題,我感覺您一直沒有停止對「魯迅遺產」的再生產。那麽,您是如何看待東南亞的「魯迅遺產」的?您認為應該如何使其成為東南亞華文文學創作中更具生產性的遺產?
黄錦樹
魯迅其實和「新南方」沒甚麼關係。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文學一直影響到今天,而魯迅在那個系統中被奉為精神導師,是「商品拜物教」意義上的,一種魔法意義上的偶像。魯迅的複雜度毋庸置疑,但大陸當代學界的尊魯似乎還是把他提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一尊北方的神。隨著論述能力加強之後,好些有能力的學者其實也在不斷的、積極的「生產魯迅」。
溫明明
除了「五四文學」傳統和左翼現實主義傳統,現代主義文學、自由主義文學、京派、海派、通俗文學等傳統在東南亞也自有其脈絡,但歷來討論較少,我覺得應該是「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在東南亞,從這個角度來看東南亞華文新文學的起源、發展或許能發現一個更加眾聲喧嘩的景觀。從您的角度,您覺得其它的文學傳統在馬華新文學中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黄錦樹
以河流作比喻,我們的南方已經是行將出海的爛泥河口(Kuala Lumpur)了。作為小文學,除了吸納可以吸收的一切,沒有其他的活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寫作以世界文學為背景,我們以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為背景。因為體量(文學人口,作品……)太小,甚麼東西到我們這裏都變小、甚至變歪,而且快速流逝,因此你說的「其它的文學傳統」即便有,也極其微渺,像爛泥上彈塗魚吐出的泡泡。
南洋一直是北方文學商品的消費市場,它的再生產能力是相對弱的。
溫明明
對於東南亞華文文學而言,「新南方」的提出,的確帶來了一些新的氣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新南方」出發討論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學者,多是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人,用一句不是很恰當的表述:「新南方」使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重新「發現」了東南亞華文文學,而傳統的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學者則較少采納這一視角。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您覺得「新南方」可能給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帶來哪些新的啟示?又或者在這種研究中需要警惕甚麼?
黄錦樹
為了避免撞上政治之牆(國籍的、政治正統的……),新南方如果不把視野限在內地(以海南島為「天涯海角」)大概只能拔高它的抽象層度,從美學風格的角度俯視,那都難免去歷史化。
我懷疑它可能會和美國漢學界和臺灣文學界近年流行的Sinophone (「華語語系」)論一樣,沒有多大的發展性。我很懷疑人民共和國的文學體制對南方「方言差異」的忍受度。
能被選擇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也是極其有限的個案。
溫明明
錦樹老師,訪談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面對許多「新南方寫作」的討論者將您和黎紫書納入其中,甚至楊慶祥還提出(「南洋」)「就在我們之中」,您是否同意或認可?這本應是第一個問題,但我有意放在最後,似乎是想為整個訪談預留一點空間,同時也期待形成一種「反諷」。
黄錦樹
和Sinophone論一樣,「新南方」論中我也是受益者,一直想保持沉默,靜靜享受紅利就好。感謝相關學者的雅意。但生而為人,帽子如果太大會遮了眼睛,也會被風吹走;鞋子不論太大還是太小,都會讓腳走不了路。
我比較好奇的是,一樣被引進「北方」,李永平、張貴興、駱以軍、西西等為甚麼沒被納入「新南方」?(如果已被納入請刪掉此句)
————
溫明明,中國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