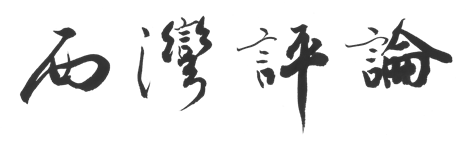丹絨馬林那棵樹
◎張錦忠

劉衍應攝影:〈吉蘭丹河〉
許多年前我的關丹同鄉陳翠梅拍了部叫《丹絨馬林有棵樹》的短片,片名見林又見樹,頗適合繞口令,所以一提到丹絨馬林我就想起丹絨馬林那棵不知道在小城哪裏的樹。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終於有機緣去丹絨馬林(似乎可以去尋訪丹絨馬林那棵樹)。
那一次由吉隆坡機場入境,然後在暮色中跨越雪蘭莪州界去丹絨馬林,其實是去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參加許德發辦的馬華文學與文化工作坊。這些年,依大中文學程在德發、月萍等同仁的帶動下,默默但積極展開馬華文學與文化的播種與耕耘工作,每年辦理依大文學季、依大文學獎、研討會或工作坊,並出版學術刊物《依大中文與教育學刊》(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成果相當豐碩。
依大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二二年的馬來師訓學院,故校園頗有些古蹟,也有不少古木,或錦樹說的怪樹,例如砲彈樹(學名叫Couroupita guianensis),研討會場前就有好幾株。會議那天,沒見過砲彈樹的與會者難免要跨過走廊邊際,到樹下去給不尋常的砲彈拍照留念。研討會的主題恰好就是「跨界與跨際」——跨越邊界,越渡文學與文化的邊際。文學的「越界」,誠然頗有值得討論與想像的空間。
其實,那天的研討會還有另外一個主題,就是「莊華興副教授榮休紀念」。一九八〇年代中葉,我回到八打靈再也二一七路十號的友聯舊址當編輯,繼續編了一年《蕉風》。彼時華興還是「成長中的六字輩」,不記得有沒有見過他,也不記得我再度來臺之後,在亞洲金融風暴前一兩年跟錦樹返馬開會時,有沒有跟他喝過咖啡烏。但後來他跟錦樹在報紙副刊討論國家文學,大推「兼語」或「跨語寫作」,同時譯介馬來新文學論述,令我印象深刻。他那些年介入論述的成果大多收入《伊的故事:馬來新文學研究》(2005)與《國家文學:宰制與回應》(2006)二書。
回想起來,二〇〇二年底我在埔里辦「重寫馬華文學史」研討會時,就邀了華興跨海來臺與會(我也邀了張光達,不過他不克前來;那些年,在馬華文學界最致力於評論書寫的人就是華興與光達)。華興那次宣讀了一篇以〈文學史與翻譯馬華:政治性與定位問題〉為題的論文;「翻譯馬華」從此變成馬華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爾後二十年間,華興與我不是在吉隆坡-沙登-加影見面,就是在高雄-臺北相聚。在我那些年的返鄉之旅,他帶我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拜訪張麗珍老師、帶我去參觀華社研究中心、去新紀元大學學院看獨大公司、去逛國民大學校園。二〇一八年夏天,我返馬開會,會後華興帶我從吉隆坡穿過東西大道去彭亨,目的地是關丹、林明、北根(中途經過文冬,我們順道去馬來文學月刊Dewan Sastera的辦事處買幾本雜誌),最後抵達瓜拉彭亨(Kuala Pahang),重訪我的出生地跟小學;這一趟「尋根之旅」,我怕他一個人開車勞累,約了友人同行。從東海岸回到都門後,他說改天我退休後返馬時,我們可以從吉隆坡驅車一路向北。
華興投入「左翼本土論述」,大概是二〇一〇年左右。彼時星柔長堤對岸的方修剛辭世,楊松年早已退休,馬華學界專注左翼論述的學者或評論者似乎後繼無人。華興的學術關注向左走,自有他的使命感。他爬梳故紙堆中漸漸消褪的左翼文學與思想遺跡,從金枝芒到馬寧、戴隱郎、伍禪,展開他可視為「重寫左翼馬華文學史」的書寫計畫。他這類文章多刊於網路刊物《當代評論》與《當今大馬》的「前夕乍曉」專欄。華興的左翼論述自有其貢獻與洞見,然而也有不見之處。寫實主義並不是普羅文學或社會現實主義文學的專利,寫實主義的對立面也不是現代主義,而如果「民國」是個時代或斷代的標籤,馬來亞獨立建國後的華文文學如果還以「民國文學」為標誌,那不就等於取消了馬華文學的主體性嗎?
二〇一七年,我執行國立臺灣文學館的新南向計畫,旨在選譯臺灣小說為馬來文,在馬來西亞出版,我邀了華興主持這項編譯工作,於是就有了《夜行/Perjalanan Malam》這本三三出版社做的臺馬小說選譯雙語本。對我而言,那也是「翻譯馬華」(翻譯臺灣作者或在臺馬華作者之外,華興將在地馬華的賀淑芳、黎紫書的作品譯成馬來文,將以馬來文書寫的華馬作者林天英、楊謙來的小說譯成華文)〔可參閱《夜行》粉專〕。那不是我們第一次做「翻譯馬華」,早在二〇〇七年左右,我跟錦樹籌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時,就邀了華興合編。那本選集將華裔馬來西亞作家以英文及馬來文書寫的篇什,藉由翻譯,跟馬華小說編在同一本書,既是以華語再現「多語華馬」,也是跨語書寫的表現,更是「翻譯馬華」的踐行。
多年以來,華興一直默默地將臺灣現代詩與馬華現代詩翻譯成馬來文,這項工作是出於他個人的興趣與熱情,並沒有兩國官方或學術單位在背後支援。然而,要在馬來西亞出版一本馬來文的臺灣現代詩選集,情況並不是那麼樂觀。二〇二二年底,在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同鄉高嘉謙動用國科會「南向華語與文化傳釋」計畫資源作為出版經費,馬來語版的《臺灣詩歌十五家》(Bunga Rampai: Kumpulan Pilihan Puisi Lima Belas Penyair Taiwan)遂由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與離散/現代性研究室出版。華興的譯詩集面世之後,我另外做了幾冊精裝本,算是送給華興的退休禮物。二〇二二年六月,華興自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退休。
寫這篇短文的時候,德發和我合編的《跨域越渡:馬華文學論集》已經出版了。編輯出版這本書的動機,自是將德發二〇二三年六月舉辦的「跨界與跨際:莊華興副教授榮休紀念暨文學與文化工作坊」所發表的論文彙整成冊,以資紀念華興多年來關心華社與國家,和他對馬華學術的貢獻,也為我們之間交往論學的情誼留念。華興在《臺灣詩歌十五家》前言寫道:
上世紀六〇年代冷戰正酣熱之際,有一批馬華青年詩人由於出生地現實情況的無奈,被迫遠渡重洋到臺灣深造。他們的精神遊走於故鄉與他鄉,形塑了一種特殊的離散心理結構,構築了當代華語語系寫作的獨殊風景。一九六〇年代以降,陸續出現了詩人與作家,有者畢業後返鄉,有些人留下,有些人留下又離開。然而,他們始終是馬華文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張錦忠攝影:〈丹絨馬林那棵樹〉
錦樹、嘉謙跟我來臺深造,不見得是「被迫」,但在臺的我輩,正是華興所說的精神遊走雙鄉(或我說的「離散雙鄉」)的那一群人。如今華興退休了,在他鄉的我們,能夠為故鄉的故人做的,大概也只有這樣了——寫論文、編輯、出版一本論文集。
那年六月間我去丹絨馬林,看到的樹很多,但那次旅程倉促,沒有去尋訪陳翠梅影片中的那棵樹。今天我在自己的校園文學院看到那株碩果僅存的印度橡樹(緬榕),想起依大校園那些奇特的砲彈樹,光陰似箭,那已是一年半以前的往事了。
*本文原為《跨域越渡:馬華文學論集》編後記, 二〇二四年六月,甲辰端午初稿,後於二〇二五年一月初補記,書出版後重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