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全都倒了,根還在嗎? ——歐大旭小說《南方》的家國政治
◎李有成
這些體認其實屬於小說家言,是離散在家國之外的歐大旭,面對馬來西亞深陷種族政治的沉痛省思與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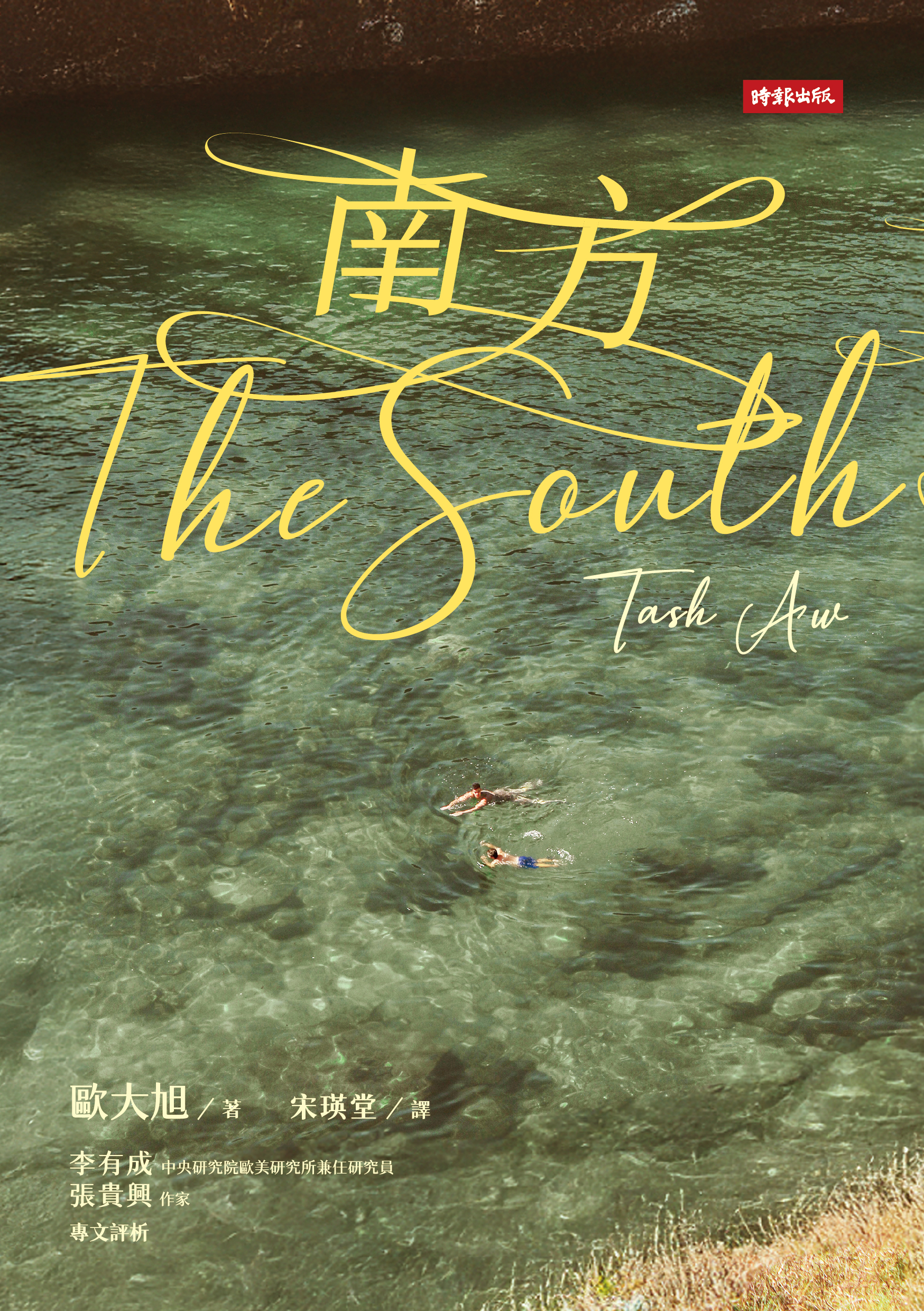
《南方》書影
歐大旭 [Tash Aw](著)《南方》(The South)。宋瑛堂(譯)
時報文化,272頁,新臺幣450元,2025年11月,平裝,ISBN 9786264199490
時間是千禧年前夕,亞洲正遭遇金融風暴的襲擊,「泰國、韓國、印尼,處境全和馬來西亞相同。」面對這個前空前的金融危機,民間和官方的說法倒是口徑一致:「都是美國的錯,……西方國家想勒死我們。」成年後的杰伊(Jay) ——小說第一人稱敘事者兼主要人物——這樣回憶:「那一年,錢是熱門話題,不只我們家缺錢,全市都在為錢煩惱。」這個時間背景相當重要,因為這場風暴對小說的空間背景也帶來衝擊與巨變。在歐大旭(Tash Aw)最新小說《南方》(The South, 2025)的敘事過程中,這個空間背景多半被稱為農場或果園,其實就是一塊「二十公頃的惡土叢林和農地」,位於馬來半島南端,而與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的柔佛州。祖父去世後,留下不多的遺產由杰伊的父親(Jack)與定居國外的兩位叔叔均分。唯一的例外是,柔佛州的這座農場卻由杰伊的母親瑞珍(Sui Ching)單獨繼承,儘管她總是輕描淡寫地說,農場「又值不了甚麼錢」,甚至還嫌「那塊地是個小累贅」。
這是小說《南方》主要情節的時空背景。杰伊記得,那年他十六歲,或者正奔向十七,離中學畢業還有兩年。大姐莉納(Lina)大他四歲,在檳城上大學,「總夢想成為藝術家,如果事業順利的話,她可以搬去香港或首爾,也考慮洛杉磯」;二姐瑩(Yin)正準備上大學,「想順著爸媽的意志攻讀藥劑學位,自己其實想當瑜伽老師」。瑩愛上一位名叫法利德(Farid)的馬來青年,他的姐姐過去是莉納的同學,不過莉納「不認為他們能修成正果」。祖父去世一年後,祖母卻因「一步沒踩穩,摔斷了髖骨,連續數星期無法動彈,從此她性情逆轉,變得難相處」。祖母與母親一向婆媳關係不佳,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婆婆對瑞珍的嫌棄,她總認為瑞珍是個拖累她的兒子的村姑。依杰伊的臆測,祖母的如意算盤是:「出身移民家庭,若想融入國家前世來生的一部分,最佳策略就是高攀世家」。婆媳不合看似家常小事,卻是牽引小說情節發展的主要導火線。在杰伊的記憶中,「那年,決定南下渡假的是我母親。」在他看來,「婆媳不合這麼多年,南下渡假而不去探望病重的婆婆,對我母親而言像是一種報復。」五口之家南下渡假的地方正是母親瑞珍繼承的農場,這不僅是少年杰伊初訪農場之旅,更是他初歷同性情慾的啟蒙之旅。他在荒野叢林與南方大城小鎮的種種冒險經歷,讓《南方》可以輕易地被納為一本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
農場距杰伊一家所居的八打靈再也不過四五百公里,瑞珍卻大費周章,「準備了一袋又一袋的衣物和食品」,莉納笑說母親「搞得像全家要移民」。——移民,或者因移民所形塑的種族或族裔關係,隱然是小說《南方》中永恆復現的重要母題(motif)。小說所牽涉的主要人物固然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從祖父母到杰伊姐弟正好三代。新馬社會過去有所謂「三代成峇」一說,只是這並不保證移民的後代可以被土著全心接納而免於結構性的歧視。譬如杰伊,只不過在學校裏行為舉止異於一般男生,竟因此飽受集體霸凌,而被異族同學出言侮辱為「中國豬死玻璃、豬國人死玻璃、死玻璃中國豬」等,其種族與性歧視直接且毫不掩飾。而杰伊的父親傑克儘管身為大學數理系系主任,照樣因微枝末節的理由不為院長與副院長所喜。依母親的說法,「問題不是他的行為,而是他的族裔。族裔向來都成問題。講開了很痛苦,但事實就是事實。」甚至小說書名《南方》,除了指涉現實中的馬來半島南部之外,對早年——尤其是第一代——離開中國,或飄洋過海,或翻山越嶺往東南亞討生活的父祖輩而言,在寓意上南方不正是他們離散之地?或者希望之地?
土地因此對這些離散華人意義特別重大。杰伊的祖父應該屬於歐大旭在其家族回憶錄《碼頭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a Pier: Portrait of a Family, 2023)中所記述的下南洋的新客。歐大旭在書中留下這樣的蛛絲馬跡:「在一九二〇年代,我外公和祖父先後冒著生命危險,乘船從中國南方來到馬來半島。當年,中國鬧饑荒,軍閥割據,內戰一觸即發,十幾歲的兩人不惜離鄉背井。」小說《南方》主要情節多採杰伊的第一人稱敘事觀點,不過也有部分情節不在杰伊記憶之內,歐大旭斷然借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觀點。在一家人初抵農場之後,瑞珍睹物思人,追憶二十幾年前未嫁時曾隨未來公公造訪農場的情景。她記得未來公公當時深陷在回憶中,一說再說不知重復了多少遍的話:「我十幾歲移民來到這國家,口袋裏沒錢,……童年在廣東,每年颱風季節豪雨成災,導致土石流,沖毀脆弱的家園,全家被迫遷徙,從新來過。」當時他就暗中許願,「總有一天,我一定要在地球上擁有一塊地,哪怕在天邊海角,只求永遠不必再搬家,死也要死在那塊土地上,讓骨頭沉進土壤,最後融入這一片歸宿。」後來他就花了一筆小錢買下位處偏遠的這塊地,即現在的農場。瑞珍很清楚,「這塊地無利潤,也不合邏輯,擁地只徒具象徵意義」。
這個象徵意義或許就是離散華人落「地」生「根」的卑微希望。在小說接近尾聲,傑克正為農場的最後命運而與管理者阿峰(Fong)爭辯不休時,杰伊竟不期然為這個議題在內心發出哲學性的思考:「人怎能在別人的土地上生活?我們相信這裏是家,讓自己在這片土地上生根——不然又能怎樣?能搬到哪裏?……內心深處,我們仍默然等著有朝一日被趕走。至於是哪一天,為何被迫遷移,我們不知道,只知屆時我們將無力抗拒。言語將無用武之地,只徒具形式,甚至顯得慌誕,因為詞句無法適切對抗或哀悼這份喪根之苦。」我們很難相信,這一連串有關根與土地、有關家國政治的思辨竟然出自時當十六歲的少年杰伊。或者出於多年以後已經成年,並深切感知種族政治無所不在的杰伊?甚至這些體認其實屬於小說家言,是離散在家國之外的歐大旭,面對馬來西亞深陷種族政治的沉痛省思與批判?
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觀點在小說中至關緊要。歐大旭顯然別有用意,他藉由全知觀點交代了小說人物的若干不堪往事,正好填補了杰伊在其回憶中難免缺漏的地方。最關鍵的是,我們發現,阿峰竟然是杰伊祖父與一位吧女所生,父親傑克因此與阿峰其實是同父異母的血緣兄弟。阿峰改善農場灌溉系統或改種鳯梨的計畫全遭傑克否定,反映的是傑克對阿峰的萬般嫌惡。在傑克看來,「憑阿峰那種出身,只有出餿主意的份」。只是反諷的是,兩兄弟雖然嫡庶有別,但是最後建議要賣掉農場的是嫡長子的傑克,而想方設法力求保住農場,為了繼承父親遺志的卻是庶子的阿峰。畢竟杰伊的祖父曾經對瑞珍說過,「這塊地是我的。是我們的——給我們的小孩和他們的小孩。」全知觀點也透露了傑克其實已經失業,甚至出軌竟達十年之久。瑞珍嘗試對兒子杰伊告白,在她無法啟齒的內心告白中,她說出壓抑心中多年的秘密:「你父親的父親也同樣外遇,長達好幾十年。有其父必有其子嘛,不用想也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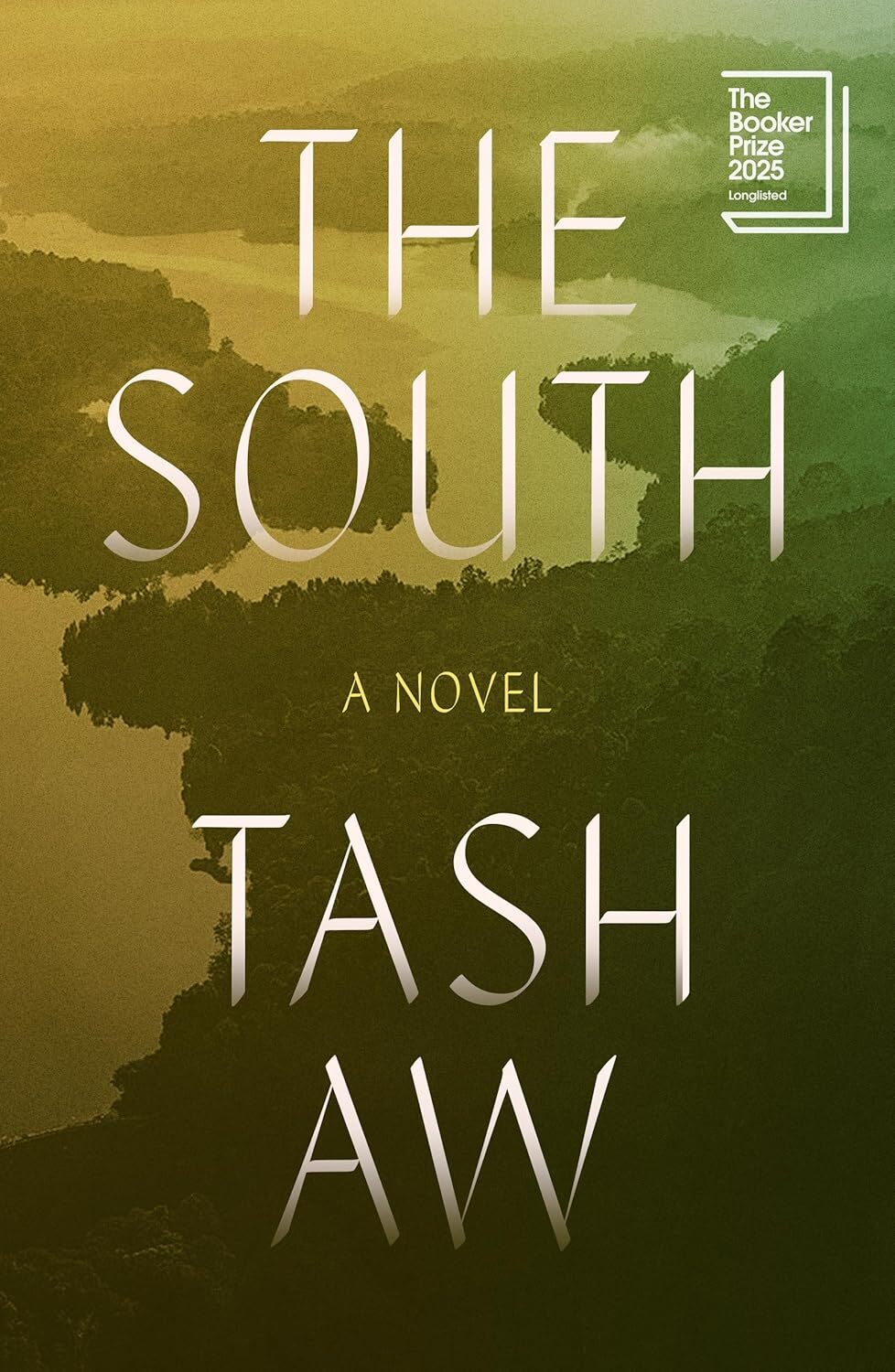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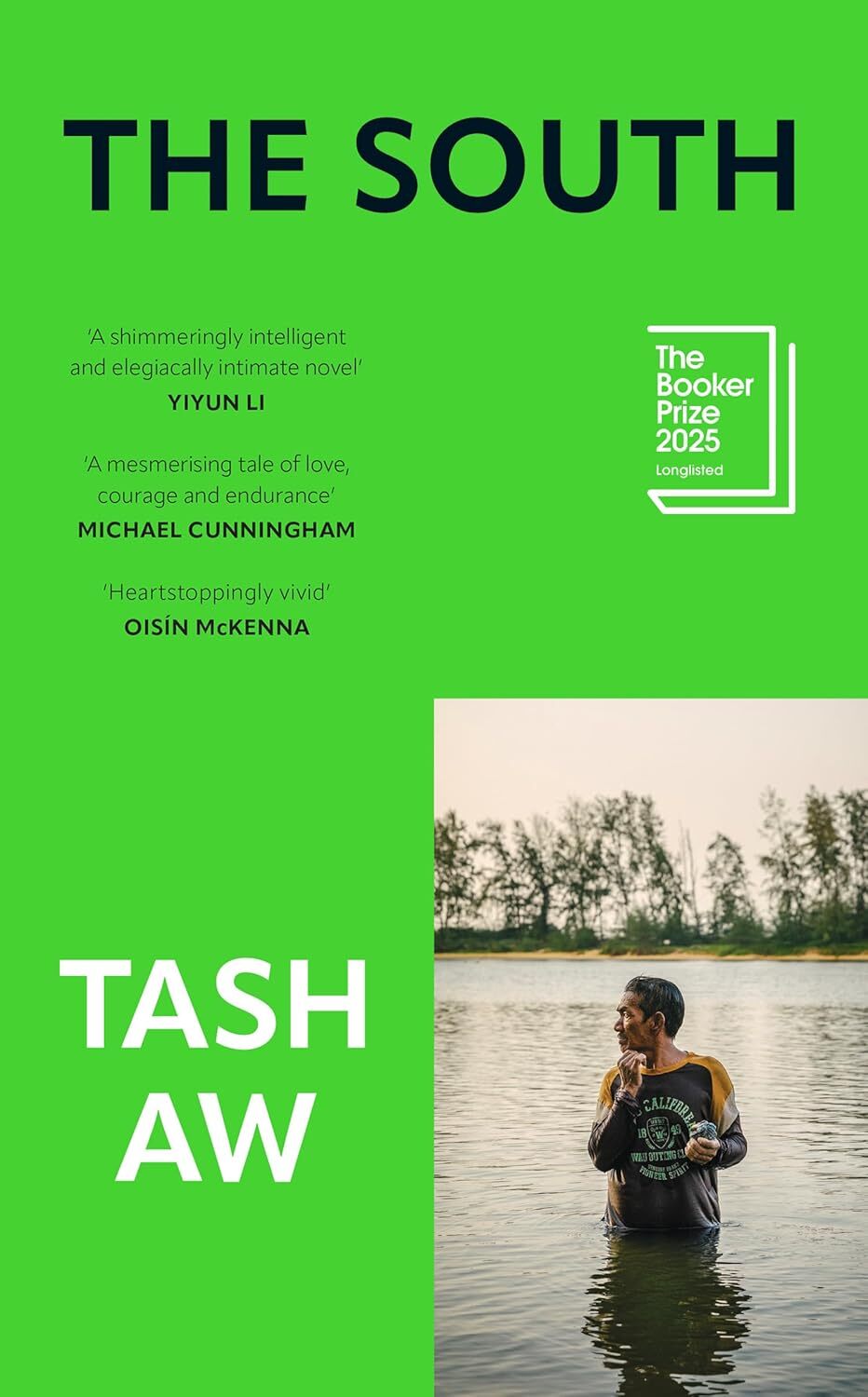
我特意簡述傑克父子兩代背叛婚姻的道德瑕疵,其實還有另一層意義,其中涉及籠罩《南方》整本小說的同性情慾的問題。《南方》在結構上始於杰伊的初次性慾體驗,地點就在農場的果園,他的對象是阿峰的兒子,十九歲的阿泉(Chuan)——在華人的親屬系譜中兩人應屬堂兄弟。這層關係難免將兩人之間的同性情慾推入倫理的糾葛狀態。杰伊短暫的農場之行最後以「兩人世界的最後一次」終。同性情慾的主題在某個意義上貫穿了《南方》的整個敘事結構,而兩人世界之外的,卻是個更為詭譎複雜的成年人的「雨雲密佈」的世界:金融風暴仍然亞洲的上空盤桓,農場的命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幾乎已成定局。事實上杰伊全家初抵農場時正值乾旱季節,「土被烤成硬塊」,在大姐莉納的心目中,農場的「正確名稱是荒原」。有趣的是,在內外交困,一籌莫展的死局裏,阿泉與杰伊熾烈的同性情慾彷彿展現了難得的生機。只是假期末了杰伊終究必須離去,在他與阿泉最後一次再訪農場,在礦坑湖邊散步時,只見「很多樹被砍伐了,空地一片片出現,看不出章法所在」。
看不出章法的當然還有面對同性情慾的家國體制。這個家國體制會以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說的規範理念(normative notion)之名,對他們的情慾自主性橫加否定;因此杰伊有一次會這樣對阿泉說:「將來我們可不可能牽手逛街——在這個小鎮或許不行,甚至在吉隆坡也行不通」。這麼說來,他們注定要流浪在家國之外,注定要成為離散的一份子;假如他們堅持他們的性慾他性(sexual alterity),他們不得不選擇現在我們常說的酷兒離散(queer diaspora)——農場容或就是他們當下所能找到的唯一的離散之地,就像杰伊祖父那輩人當年離鄉背井,渴望擁有土地的那些「碼頭上的陌生人」。從土地到情慾,從第一代移民到第三代,雖然個別投注的感情不同,家國體制始終形影不離,藉不同的面貌,以種種歧視的技藝,對個人或群體施行有形或無形的暴虐壓制。在我看來,這樣的家國政治正是小說《南方》敘事結構中若隱若現的政治無意識。
杰伊在他的記憶中並未提到農場的最後命運,可以想像農場終將易手,未來或以其他不同的面目與意義存在。小說《南方》臨結束時,阿峰「渾身怒火全轉給鏈鋸」,奮戰不懈地砍伐一棵羅望子老樹。過了幾天,杰伊與阿泉發現,「羅望子樹已經全被鏈鋸夷平,凌亂堆疊在地上,彷彿一場風暴心一橫,專對農場這一區肆虐撒野」。樹全都倒了,根還在嗎?根不在了,家呢?這莫非是歐大旭新小說《南方》對家國政治的肆虐留給我們的省思。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於臺北
──────────◎李有成,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現為該所兼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