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文學與文化評論:李奭學教授訪談錄(上)
主訪人◎單德興
時間: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
地點: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三樓會議室

李奭學接受單德興訪問。(單德興提供)
|前言
李奭學教授為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為華文世界著名的學者、譯者、編者與書評家,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外文學關係、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中國翻譯史以及現代文學。
李教授多年勤於筆耕,著述、翻譯、編作甚豐,學術論述有《中西文學因緣》(1991)、《經史子集:翻譯、文學與文化評論》(2005)、《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2005)、《三看白先勇》(2008)、《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2012)、《中外文學關係論稿》(2015)、《明清西學六論》(2016)等;書評有《書話台灣:1991-2003文學印象》(2004)、《台灣觀點︰書話中國與世界小說》(2008)、《台灣觀點︰書話東西文學地圖》(2009);譯作有《余國藩西遊記論集》(余國藩著,1989)、《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孫康宜著,1992)、《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孫康宜著,1994)、《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Michael Payne著,1996)、《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余國藩著,2004)等;編有《異地繁花︰海外臺灣文論選譯》兩冊(2012)、《古今聖經殘稿》九冊(賀清泰譯)(與鄭海娟合編,2014)、《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四冊(與林熙強合編,2014)、《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四冊(與胡嘵真合編,2015)、《中外宗教與文學裏的他界書寫》(與黎子鵬合編,2015)、《古新聖經殘稿外二種:北堂本與滿漢和璧本》(與內田慶市合編,2018)、《清代基督宗教小說選注》(與黎子鵬、吳淳邦合編,2018)等。
由於李教授在各方面表現傑出,曾獲中國時報開卷周報推舉為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評人(2001),並先後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2003)、東吳大學建校一○五年傑出校友獎(2004)、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2010, 2011)、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011)、胡適紀念研究講座(2019)、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2020)。此外,《書話台灣》獲選《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2004),《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獲第三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2014)。
主訪人與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多年同事,雖然分屬歐美研究所與中國文哲研究所,其實同為比較文學出身,並從事翻譯研究與實踐,因此有不少交集之處,並經常交換研究成果與著述。主訪人於二○二○年九月致贈《擺渡人語:當代十一家訪談錄》時,曾表示希望有機會與李教授進行深度訪談,終能在次年三月順利完成。因為內容廣泛,前後進行兩次,現場同步錄音與錄影。訪談錄音由趙克文小姐繕打,趙麗婷小姐與陳雪美小姐協助編輯,由主訪人校訂後兩度送請李教授過目並確認,謹此致謝。
|成長背景
單德興
首先請介紹家庭環境與成長背景。
李奭學
我們家位於臺北縣三重市二重埔,是個很普通的臺灣人家,家裏最早是務農。祖父時代,家裏有很多田;我爸爸還是一手牽著牛、一手讀書。他後來考上建國中學、淡江英專,最後再到明志初級中學教書。我小時候家裏還在務農,有牛棚,臺灣話叫「牛稠」。聽長輩講,日據時代家裏還養有馬。我玩過打穀子用的打穀機,就是單腳踩,把穀子和稻穗打分開來。家裏不再務農後,就開了碾米廠。爸爸一邊當老師,一邊當小老闆。碾米廠設施頗有一套。我常跑到噴出米糠的工作房,噴得滿身都是米糠。常看到爸爸用頭巾綁頭,穿上工作服,走進米糠區。我小時候喜歡在米糠堆裏玩,因為米糠軟軟的,幾個小孩子就在裏面打滾。
單德興
我對米糠有印象,小時候南投的中寮鄉農會有個大倉庫,裏面都是米糠,一大包米糠其實滿輕的,而且價錢便宜,我們常跟賣米糠的人一直說「賣便宜一點啦!」結果他乾脆用送的。
李奭學
我對這些都還留有強烈的印象,像是堆成一堆堆的稻草、曬穀場,我都親眼目睹過。我家那條街叫五谷王北街,因為有一座供奉神農大帝的「五穀王廟」,後來把「穀」改成山谷的「谷」,可能因為可省不少筆畫。1 我們家門外就是灌溉用圳溝,兩邊有稻田,也有種蔬菜的。但是過了農業區的對街,就是工業區了,叫光復路。我們農業區的小孩若不想升學,想早點賺錢,很簡單,就跑到工業區去應徵。工業區有很多鐵工廠,小時候的玩伴後來幾乎都當了鐵工,是黑手人家。我們家算是白領階級吧,其他親朋好友大多也是務農。
單德興
你名字中的「奭」字滿有學問的,考倒不少人,是家族的排名嗎?
李奭學
爸爸是英文老師,不是中文老師。我曾問爸爸,怎會選這個字?他說是自己查字典找的,因為我是老大,所以特別下工夫選字。我不知道跟五行、筆畫有沒有關係,也沒有問爸爸。小時候最常被人問到的,就是名字中的這個字了。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只有一位國文老師拿著點名冊,可以馬上叫出李「奭」學,但我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有沒有做功課。「奭」這個字,其實早在周朝之前的青銅器上就有了,上古時期有不少人用,漢唐以後用的人才慢慢少起來。據日本漢學家白川靜的古文字研究,青銅器的銘文上可以找到「奭」字,白氏還做了一番解釋。西周初期,與周公一起輔佐周成王的召公也叫奭。這個字大概很早就傳入韓國、日本,印象最深刻的是,到韓國開會時,看到很多人用「奭」字。朴正煕之前有位李範奭,是大韓民國建國後首任總理。有一次我到韓國開會,來接機的是個英文系學生。我用英文問他,念得出我的名字嗎?他說這個字很多韓國人用,當場就用韓文念出,跟中文差不多,也跟臺語(sèk)差不多,日文sè-ki只是把尾音拉長而已。
|小學與中學
單德興
你的小學與中學經驗如何?
李奭學
我其實是不大喜歡讀課內書的小孩,整天都在玩。在學校最快樂的時期是國二以前,小學時根本不讀「正書」,看了很多「東方少年文庫」之類的世界文學名著改寫本。我是第一屆國中生,但惡補到小六上學期,才從《中央日報》看到要改制成國中。但老師說報紙寫得不一定準,所以繼續補習。到了小六下學期,我都還在惡補。
單德興
是哪所學校?
李奭學
二重(國民)小學。我家從祖父起,都從這所學校畢業。祖父是他們兄弟間第一個識字的,日據時代當保正,國民政府時代是里長。我小學畢業後讀穀保中學,是一所私立學校,2 現在還在,變成穀保家商。改為直升國中之際,臺灣沒有那麼多公立學校可用,像穀保中學這種私立學校就被找去協助,叫「代用國中」。穀保中學是在田間的學校,二重國小附近大部分也是田。那時候我上課心不在焉,常常跑去埤仔游泳,回來被老師罵,甚至還被揍。一直到穀保中學二年級之前,我爸都放任、隨我去。直到快三年級,他看情況不太對勁,才把我從穀保中學轉到他任教的明志中學。
單德興
是公立的?
李奭學
對。本來是省立臺北商業職業學校(簡稱「北商」),後來這家「北商」遷出去,原址成立明志(國民)中學。我爸原先在萬華女中教書,後來轉到明志中學,就在家附近。爸爸當了不知多少年的教務主任。我國中三年級之前,他真的甚麼都不管,但當時還要考高中,就把我找回到他任教的學校就讀。若不是這樣,我說不定也當黑手了。三年級我開始嘗到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對我們來講,人生辛苦莫過於開始要求考高中、考大學的階段。我就這樣進了建中。
單德興
好好念一年書就考上建中,那很厲害啊!
李奭學
我父母雙方的家族建中、師大附中畢業的不少,我爸爸、舅舅、叔叔都是。我覺得很奇怪,爸爸這邊務農,媽媽那邊打鐵出身,可是幾個長輩都是大學畢業。我爸是淡水英專,後來拿到改制為學院的文憑,算是親戚就讀的學校中最差的。其他的像舅舅,都是念國立大學。那時候沒幾間國立大學。我從美國回來之後,才發現多了一大堆學校。我可能跟你不大一樣,我不太想離開臺北到外地讀書。大學考了兩次,第一次按照外文系的志願排序,從臺大一路填下來,結果考得不理想。我爸要我重考。
單德興
有補習嗎?
李奭學
我跟補習班沒緣。錢繳了,南陽街去了一次,就沒再去,回家自己讀。其實上半年我也心不在焉,都在玩或看一些外國文學名著的翻譯本,現在可以想起來的有《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與《曼佛雷得》(Manfred)等。下半年轉到姨媽家住,才循規蹈矩地念起聯考要考的「正經書」來。
單德興
我因為在南投鄉下學校,理工科師資很差,絕大多數同學不得不考社會組,因為靠著背誦在聯考還有機會一拚。照說建中以理工科為主,你怎麼會選文科?
李奭學
我想是個性使然吧。我課外書讀很多,數學很差,聯考的數學等於放棄,別人總分六百分,我總分只有五百分。
單德興
我們在鄉下,許多同學放棄數學,我聯考數學考了三十分,算是不錯的了。因此我一直認為,如果一個教育政策使得那麼多學生放棄學習一個科目,真是罪大惡極,完全沒盡到教育的責任。
李奭學
建中也滿多念文組的人放棄數學。我在東吳英文系,建中、北一女畢業的有一些,多因數學太差而來。還有就是興趣的問題。第二次考試,我以為應該沒甚麼問題了,看起來比較有出息的大概只有英文系、外文系,所以我一路就填到輔仁大學,連中興、中央我都沒填。因為我外婆家在新莊,我從小就在輔仁大學裏騎著腳踏車逛來逛去。
單德興
只填北部的英文系、外文系?
李奭學
對。結果考試下來,我居然上不了輔大英文系,就到了東吳英文系。
|大學時期(1975-1979)
單德興
輔大英文系和東吳英文系都很有歷史。
李奭學
是的,不過輔大英文系一向分數很高。我的聯考分數上得了成大,也上得了臺大中文系,都因為志願填寫的緣故跑到東吳念書。
單德興
當時外文系開設的課程都在朱立民、顏元叔改革之後,有沒有甚麼印象深刻的老師或課程?
李奭學
我在東吳英文系,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三個老師。一個是邢光祖,教我文學批評,他那時候年紀滿大了,當時好像是政治作戰學校外文系系主任。政戰學校的外文系是真的外文系,管了一大堆日文、德文的軍校生。我叔叔在世新教書,幾年後巧遇邢光祖,邢先生居然還記得我的名字,可能因為中間那個字太特殊了。我這一門課始終都是高分。李本題的英國文學史,我滿喜歡的。再來就是教英詩的蘇篤仁,他本來和英詩一點關係都沒有,是系上請來教英詩的。他雖然是日本式的發音,但太太是美國人,所以念起英詩來還是抑揚頓挫,很有味道。那時候的英漢字典,如果是袖珍本的話,最流行的就是大陸書店出的那一本《大陸簡明英漢辭典》,是蘇篤仁與陳本立合編的。3 蘇老師大學唸台大外文系,但這之前的小學中學受的都是日本教育,日文相當好。他曾透露,他那本字典其實是拿三省堂的字典作底本,把日文解釋挖掉,再填上中文解釋,然後翻拍,所以很少地方排錯,因為日本人做事很嚴謹。還有柏子仁的歐洲文學印象也很深,可惜他英年早逝。
單德興
那時候的課程,基本上是把新批評那一套搬過來嗎?
李奭學
教文學批評的邢光祖是從柏拉圖(Plato)開始,然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一路下來,用的是 W.J. Bate 編著的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Enlarged editio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4
單德興
大學生就用那一本?可真不容易。
李奭學
對。所以我還滿熟悉希臘上古以來的文學理論。後來到輔仁大學念研究所,當時謝德樂(Donna Schaefer)教我們文學批評,我上了一、兩堂之後,跑去跟所長康士林(Nicholas Koss)說,這門課我實在熟,於是他跑去跟謝德樂談,謝德樂居然讓我免修了。
單德興
他們沒有稍微問一下你熟到哪個程度?
李奭學
沒有。
單德興
完全相信你。
李奭學
對。所以大學部的文學批評這門課,對我影響滿大。新批評則是跟一個教小說的美國女老師學,她教小說完全用新批評的觀點,非常認真。
單德興
用的是Understanding Fiction?
李奭學
對,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人編寫的。5 長篇小說讀的是那時最流行的俄國作家索善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癌症病房》(Cancer Ward)和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我印象是,不論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我們一律用新批評的方式閱讀。
單德興
讀索善尼辛用的是英譯本?
李奭學
對。對美國人來講,反正讀英文就對了。國文方面,東吳大一、大二都有國文課,我一路從黃登山到曾經在故宮圖書文獻館任職的吳哲夫,成績都是擦邊球,因為我很討厭背書,在中學已經背了六年書,到大學還要再背書!考試時背書五十分,其他申論題五十分。
單德興
我那時政大的大一國文要會考,默寫占四十分,擺明了不背書就過不了,不但像我這樣討厭背書的臺生覺得受不了,許多僑生更是戰戰兢兢,深以為苦。
李奭學
東吳的國文不採會考,是由老師自己來。同學們都在背書,但我不強求自己,能背多少算多少。有一次被當,只能補考,不然還要重修,只好硬著頭皮背了。
單德興
我一直很好奇,我們這一代都是在臺灣受同樣的國文教育,但我很佩服兩位外文系出身的中文造詣,一個是你,一個是彭淮棟,我臺大外文系碩士班同學。你說自己不愛背書,那你的中文是怎麼練出來的?
李奭學
跟你的老師余光中很有關係。他的任何文章都有一股氣勢,像我這種喜歡文字的人很喜歡看,會跟他學。他出的任何書,我在大學、研究所時代幾乎都讀過,一直到我出國,出版社還會寄余光中的新書給我,請我幫他們寫書評。因此,余光中對我的中文影響很大。楊牧、顏元叔這些人對我的影響則是,若想要當作家,最好去念個博士,才能有像樣的職業養家活口。余、楊兩人常寫詩、寫文章,那是副刊全盛的時代,在副刊上常常看到他們的文章,無形之中就會天真的覺得,當教授可以很快活地想寫甚麼就寫甚麼。當時在臺灣當教授,也不必非得念個博士不可。我研究所畢業後在現在的真理大學(以前叫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教了一年的書。讓我喜歡寫文章,影響我求職方向的應該是顏元叔和楊牧,還有夏志清。影響我文字的是余光中,楊牧的文字沒有人學得來。顏元叔有時候很凶悍,有時候看一看、笑一笑,吸收一下他的知識,卻也無從學起。余光中的散文我一看就很喜歡,倒沒那麼喜歡他的詩。他在純文學出版社出的書,幾乎每出一本,我就買一本來讀,還寫了書評。後來認識余光中,我也沒機會跟他多談這方面的事。不然,他應該覺得做了一些好事,影響到像你、我之類的年輕人。
單德興
對。余老師的文章我當然也會看,尤其大二當他學生的時候,但沒像你這麼認真。你是甚麼時候決定讀碩士班的?
李奭學
大約大二下學期就決定了。我跟你一樣,覺得不要浪費時間考預官,不一樣的是,我先去當兵,從大專兵開始,到最後副營長給我掛了個下士。我在虎嘯部隊,最早在營部當文書,那裏的預官學歷都沒有我高,也不大管我,所以我當文書兵很快樂。新竹關東橋訓練後,下部隊守八里海防。我們部隊到的地方還真多,八里待了兩、三個月,就拉到林口。我們旅部在林口,而林口和八里離我家二重都很近,我又是文書兵,常常有機會回家看看。不過,當兵最快樂的不是在林口或八里,而是在小格頭,位在北宜公路下的一個山谷裏面,旁邊就是鯉魚潭。我們部隊撤走之後,鯉魚潭就封了,變成翡翠水庫,我們營區也變成水庫的一部分。那個地方真是天高皇帝遠,就只有我們一個營。師部在關渡,師長要來,我們在北宜公路上的哨兵老早就知道了。即使師長真的來,也得經過三十分鐘,走很彎曲的一條路,才能到山谷下面來。我們營長點不點名都無所謂了。後來我又跟營長跑到樹林的三民主義講習班,他去當大隊長,我幫營長做點文書工作,其實也沒甚麼事,每天除了準時上床睡覺之外,我就看自己的書。
單德興
讀的是考碩士班的書嗎?
李奭學
不是。那時候還沒想到考試用書。我不像楊牧那麼浪漫,帶一本濟慈的書信集去當兵。6 我是帶一本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 The Canterbury Tales[《坎特伯里故事集》],因為我滿喜歡敘事文學,那本書在課堂上一直都沒讀完,想說當兵時間多,有機會就讀。那本書我從樹林的講習班起都帶在身邊,後來我隨部隊打前戰,也帶去了金門。部隊住在中央坑道裏面,後來又調去守海防,在碉堡裏住。我是在碉堡裏退伍的。你記得當年著名的少棒投手許金木吧?我跟他同年同梯次,退伍的時候他就站在我前面,先叫他名字,然後叫我的名字,再上船。當兵生涯不能說沒有收穫,我還是覺得當時不考預官的決定是正確的,拿那個時間來讀別的東西快樂又有益。
|碩士班時期(1981-1985)
單德興
如何銜接上研究所的?
李奭學
大三開始我的成績漸好,已經在準備考研究所。當兵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六月多,研究所都考完了,我們在外島也不可能讓你請假回來考,只好跑回東吳當助教,第二年才考,沒考上臺大。我當助教,對面坐的是陳界華,他那時在臺大外文研究所念書。他跟我說既然沒考上臺大,應該到輔大去,因為臺大很多老師是從輔大請來的。我也不想重考。當年輔大錄取五名,我是最後一名,呂健忠是第一名。
單德興
還記得是哪五位嗎?有繼續在學界發展嗎?
李奭學
有位監玉龍,後來在師大英語研究所念博士;高寒梅,在公共電視工作,後來聽說到香港工作;簡素琤,是輔大比較文學研究所早期的博士。常在一起上課的另有吳信鳳,哈佛教育系的博士;還有孫小玉,是印第安那大學的比較文學博士。呂健忠的太太一直叫我催呂健忠考博士班,要不就出國念,可是我一直說服不了他。他大概鐵了心,覺得翻譯對他來講比較有意義,不願意浪費時間念博士。他譯過很多希臘古典文學,本本都是精心之譯,如今想想,他或許對。
單德興
你覺得從輔大獲益最多的老師或事情是?
李奭學
輔大倒真的是改變我很大的一所學校。當時東吳的老師沒有給學生很強的世界觀,可輔大就不一樣了。雖然都是一些神父、修女、修士,可是這些人都是大學校出來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請他們幫我寫推薦信時,因為沒錢申請美國名校,就拿了一些州立學校的名單給他們。他們不大想寫信,對我說:「你是我們最好的學生,為甚麼要到這些學校去念書?」他們沒想到,哈佛、芝加哥這些名校的申請費都在六十到七十美元間,那時是美元兌臺幣一比四十的時代。我在東吳兼任助教,一個月薪水五千塊,申請兩間大學校,一個月薪水就快沒了,難道要整個月喝西北風?後來是輔仁大學英語研究所拿錢讓我去申請學校。我申請時從哈佛一路排下來,排到芝加哥大學,算一算剛好是美國前四名的大學。後來跑到芝加哥去念書,跟我的指導教授歐陽瑋(Edward P. Vargo)很有關係。他是芝加哥英文系出身,當時已寫了一本有關厄普代克(John Updike) 的書,7 他的建議我大多會接受。談德義神父(Pierre E. Demers, SJ)倒是沒有像歐陽瑋或康士林那麼要求(demanding),比較不會在意我要讀甚麼學校。
單德興
你跟談德義和歐陽瑋那些老師都修些甚麼課?
李奭學
他們的分工是談德義教詩,歐陽瑋教戲劇,賀永光修女(Sister Heliéna Krenn) 教小說,其他人就教一些其他文類或主題。第一次上康士林的課是研究方法與書目之類的,是相當嚴謹的訓練。臺灣當時只有五個英語研究所,都在北部。8 只能把這五個學校的圖書館當作一個圖書館來查閱資料,頂多加上耕莘文教院和臺北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我跟康士林念了費茲傑羅(F. Scott Fitzerald)的專題,跟著歐陽瑋把整個世界戲劇史跑了一遍,上下學期整整一年的課;又跟白行健(Stephen Berkowitz)念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歐陽瑋每堂都考試,很可怕。有些同學考得亂七八糟,可是我每次考試都九十分以上、甚至一百分。
單德興
有甚麼秘訣嗎?
李奭學
沒甚麼秘訣,就是把書讀得很熟。歐陽神父主要是怕學生上課前不讀書;對臺灣學生來說,不備課是很自然的嘛。要避免這種情形的唯一方法就是堂堂考試。我們那班真的能夠坐下來討論,因為每個人都讀了書,差別只在有沒有讀熟。跟歐陽瑋上世界戲劇,宛如轉了世界一圈,他自己也跑了一圈。後來又上了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我碩士論文寫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9 他是莎士比亞之前的悲劇大家。
單德興
怎麼會想寫馬羅?
李奭學
大概因為柳無忌的緣故,他譯了一本《英國文學史》,10 裏面介紹到馬羅,說他的詩行非常有力,引了一些例子,讀起來果真鏗鏘有力,所以我就跟歐陽瑋說,有沒有機會上馬羅的劇作?輔仁大學學生少,可以商量下學期要上甚麼課。他說有詩又有戲,可以開課,就這樣讀了。
單德興
記得我那時候是跟余光中老師在英國文學史的課上讀馬羅的《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
李奭學
這是他最出名的一齣戲,到現在有很多詩句我都還記得。我這輩子講英語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輔仁大學,比在美國念書時還多。我到芝加哥大學跟余國藩教授讀書,他找我聊天,練習國語,所以很少跟我講英語。我們全家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回到家也是講國語,只有在課堂上說英語,不像在輔仁大學,課內、課外一律是英語。白行健是哈佛英文系畢業的,在輔大教了十幾年書,他不是神父,我們常來往。除了上課外,學生也會找老師吃飯。有時候我就到修道院吃頓晚飯。研究所小,這些事好辦。研究所畢業選學校,我對《西遊記》、米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和史賓賽(Edmund 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興趣盎然。康士林、歐陽瑋和白行健都說芝加哥是最好的地方,再加上歐陽瑋是芝加哥出身,我大受影響,就跑到芝加哥讀博士。
|博士班時期(1986-1999)
單德興
你是在輔大學的拉丁文嗎?
李奭學
不,輔大連第二外語都沒要求我們考。對這些老美教授來講,你們英文都還不夠好,讀甚麼其他語文?我的日文是在東吳上的,念了兩年,到芝加哥又念了兩年。我去的時候,芝加哥的比較文學系還是個「委員會」,稱作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Literature,後來才變成系的,也就是可以開設大學部,讓本科生選課。芝加哥大學的語言要求不高,英文不能算,所以我選了德文、法文、中文。到了要做博士論文前,余國藩老師跟我說:你不懂南歐語文不成。我只好跑去聽課,買書回來,從義大利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文法都走過一遍,單字沒背很多。我法文讀得還不錯,從法文字可以抓英文字,從英文字可以抓法文字,法文有些跟義大利文又相通,同屬於拉丁語系。
到了最後余老師說,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他們的主要語言是拉丁文,你不能不懂。那時候我都已經第七年級還是第八年級了,余老師要我去讀拉丁文,不然就不讓我寫博士論文。我只好去讀,拉丁文變化多得不得了,在班上正式讀了一年,再到補習班補了一年,還是必須拿字典查。希臘文去了半學期就落荒而逃,因為當時年紀太大,已經三十五歲了。如果楊牧在,他會跟你說,二十五歲之前最好把這些東西都學完,之後不要再想學這些語言了。不過,我在英文系的老師繆倫(Michael Murrin)倒是跟我說,他在三十幾歲才開始學希臘文,鼓勵我多讀。
單德興
芝加哥大學的訓練非常扎實,但是時間比較長,心理上會不會有壓力?
李奭學
當然會有壓力,主要是經濟壓力。我一九八六年就出國了,那時候倒沒有想到將來服務年資之類的問題,隨時想的都是要申請甚麼地方的獎學金,從學校的博士論文研究學人(Dissertation Fellowship)開始,一直到校外的伍德羅.威爾遜基金會(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的獎學金,連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新光文教基金會的獎學金我都拿過。最後申請到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的經費。中國文哲研究所的彭小妍說你最好回來。回來之後,我就自己關在研究室裏專心寫論文,那是在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拿到博士學位,才算「正式」回國。
單德興
那時候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剛開始沒多久。
李奭學
這我倒是不知道,在我之前好像還有呂妙芬。11
單德興
現在你們兩位在中研院都很資深了,呂妙芬都當上了近史所所長。
李奭學
我讀博士時,其實上了一、兩年課就曾回臺灣工作了一段時間,在《聯合報》系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當翻譯。你倒沒有去。
單德興
我那時正好在高雄鳳山服兵役,不過我知道很多外文系出身的人去了那邊,包括李有成、彭淮棟。
李奭學
對,我就是在那邊認識阿棟及有成兄。有成兄說中央研究院剛成立文哲所,可以投個履歷表去申請當研究助理,不過我沒有投,回芝加哥去了。回來文哲所寫博士論文前,因為自知我做的題目在臺灣書籍會比較少,尤其是西方的相關書籍,所以自己買了一台小影印機,印了一大堆博士論文及其後可能有用的書。12 我辦公室還有一大堆自己印的書,把這些帶回臺灣才有可能把論文寫好。屬於耶穌會的中文材料在臺灣找得到,可是屬於西方的證道故事(exemplum)這部分,臺灣根本沒有,我是從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一本一本找出來,影印帶回來看的。
|耶穌會證道故事研究
單德興
當初博士論文怎麼會想要做這個題目?
李奭學
這也是一件怪異的事。本來我是一個連基督教、天主教都分不清楚的人,去輔仁大學讀書之後,開始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並不一樣,至少宗派不一樣。我也了解到談德義是耶穌會的神父,歐陽瑋是聖言會的,康士林是本篤會的,開始知道不同的天主教修會。這其實沒甚麼,但有一天我到文學院圖書館,抬頭剛好看到一套李之藻編的《天學初函》,收了利瑪竇、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等人在明朝翻譯或撰寫的書。
如果不是在輔大念書,看到《天學初函》這個書的總題,大概就走過去了。但是考大學的時候,我從中國文化史裏知道,天主教最早在華集結成書的是《天學初函》,而這書跟耶穌會尤有淵源。因為談德義的關係,我很好奇,就拿下來看。第一本看的是利瑪竇的《畸人十篇》,13 發現裏面怎麼有這麼多小故事,甚至有《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裏的故事,實在很難想像。因為我們讀中國文化史時,只說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出版《天學初函》,把西方科技介紹到中國。《天學初函》後面確實有《幾何原本》之類的書,可是前面幾本是很人文的書。
單德興
他們就用「伊索」這個名字?
李奭學
他們是用拉丁音,阨瑣伯(Aísôpos)。伊索(Aesop)一部分的生平、寓言也寫進去了。我覺得很奇怪:證道不用耶穌的比喻,卻拿教外的東西,道理在哪裏?有了這些謎團之後,我也沒去問那些老師,問他們大概也不會知道。於是我就自己研究,寫了一篇〈希臘寓言與明末天主教東傳初探〉,投給《中外文學》,登了出來。14
單德興
這是你正式刊登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嗎?
李奭學
可能是。我應該寫於研二的寒假吧。那篇文章寫出來之後,就忘了這檔事,又開始讀跟攻讀碩士學位相關的英美文學(我的副修是美國自然主義小說)。後來到芝加哥讀書,還是得從頭讀起,所以又從比較文學概論開始讀,等於重新繞了一遍,讀了一個比較文學的碩士。只是系主任說,我承認你在輔仁大學的碩士學位,但是第一年的九門課你必須上完,碩士論文要寫完。至於畢業證書呢?他們說你已經有了一張碩士畢業證書,還要第二張幹嘛?
單德興
不抵博士班學分?
李奭學
抵得不多。
單德興
有哪些印象比較深刻的或受益的課?
李奭學
中世紀英國文學,那門課由一位剛從劍橋來的女老師授課,真的長了我不少知識,就直接讀中古英文(Medieval English),上了不少。跟貝文頓(David Martin Bevington)又上了Medieval Drama(中世紀戲劇),跟另外一個女老師上Medieval Literature(中世紀文學)。余國藩還是上希臘悲劇和Christian Classics,我另和我的太老師格林(David Greene)、神學院的杜尼格(Wendy Doniger)及崔西(David Tracy)、馬基恩(Bernard McGinn)教授也上過莎士比亞、希臘悲劇和神學思想史等課。後來賀米.峇巴(Homi K. Bhabha)來了,我也跑去上他的後殖民主義的課。
單德興
余國藩他們是用希臘文上嗎?
李奭學
余國藩他們用希臘文,我們學生懂得的就讀希臘文,不懂的就只好讀英譯了。他們神學院懂希臘文的人滿多的。這些都是印象很深的一些課。繆倫教Faerie Queene專課,他甚至連Fairy Tales都教。他是寓言(allegory)的專家,著有The Veil of Allegory等名作。我剛到的時候,他說你運氣不錯,這本書剛剛再版,學術書再版的實在不多,我送你一本。15
到了芝加哥,又要寫碩士論文,我得思考要寫甚麼。他們所謂碩士論文是叫 M.A. paper,比一般學期報告長,大概到四十頁左右。他們說,就算你拿到博士,還是照樣要寫碩論。我又想到《伊索寓言》這個課題,再去翻了很多耶穌會的東西,愈找愈多,後來發覺耶穌會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至少翻譯了將近六十條左右的《伊索寓言》。日本是把整本三百多條的故事在十六世紀末如數譯出,在中國只譯了六十條左右,一六二五年出了一本專書。16 因為要寫碩士論文,所以我又想起這是一個可以做的比較文學題目,就跑去跟繆倫談,他那時候是我的導師。他說這是個好題目,你應該繼續做下去,我就繼續做下去了。
碩士讀完之後,我把這個題目又擺到一邊去,等到要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才又想起來,重新開始思考:我研究了這麼多異教的tales,包括前不久在胡適紀念研究講座裏談的西洋古典軼事,17 覺得傳教就傳教,為甚麼還夾雜著一些教外的故事?我先問余先生,他說不知道。我就從神學院問到英文系,再問到古典系,一路這樣問,大家始終都跟你說聽起來很熟悉,但講不清是甚麼。我因為一點神學背景都沒有,遵余先生之命到神學院讀了兩年書,研究講道(preaching)的方法,才發覺其實 “exemplum” 這個字我和呂健忠在翻譯《西洋文學概論》時早就譯過了,當時譯成「示範故事」。18
我們翻譯此字時,沒有把宗教問題帶進來,所以一點也不知道跟證道(sermon)有甚麼關係。後來發覺證道辭裏夾雜了大量這類型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等人的故事、《伊索寓言》,甚至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的故事等等,我才了解從西方上古到文藝復興,這些故事是常見的講道修辭例證,雖然我老早就知道這個字了。我查到這一點,很高興,之後就決定寫明朝所譯的這類故事。
碩士論文既然寫了天主教士與《伊索寓言》之間的關係,博士論文就應該擴大。《伊索寓言》我比較能掌握,另外有一種文類還是很難了解是甚麼:chreia。劉義慶《世說新語》裏面的「世說」(明朝時這是種文類的名稱)或劉知幾《史通》裏所謂「瑣言」,大致可以概括這種文類的形式與內容,因此我以「世說」為之定名。且舉有關亞歷山大大帝的一則世說為例。他有一次去見希臘犬儒學派的大師、創派者戴奧吉尼斯(Diogenes of Sinope),對戴氏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那麼我寧可是戴奧吉尼斯。」戴氏的回答是:「如果我不是戴奧吉尼斯,那麼我還是不願當亞歷山大。」
在明末,這一類的故事耶穌會士翻譯了不少進中國。我本來以為約略一千條左右,最近整理才發現,明末的總數至少有四千五百條到五千條左右。我當學生時,其實一直沒辦法理解像亞歷山大這類的故事是甚麼,後來在研究聖經文學的時候,無意間看到有篇文章說,耶穌很喜歡用"chreia"這種文類來布道。深入探究之下,才了解"chreia"這種文類正是前述亞歷山大這類故事的名稱:簡短的一個故事,主人翁可因他人發問而講出一些極富智慧的話來。
我的博士論文其實可以闡述更多的發現,但當時已經讀了十幾年書了,所以就把題目限定在古典型證道故事(classical exemplum)上,Christian exemplum (天主教證道故事)待以後有時間再處理了。坦白說,沒有人能告訴我這些故事的來龍去脈,所幸芝加哥大學有一座非常棒的圖書館,幾乎甚麼書都找得到;就算找不到,透過館際借閱也能調得到。我自己有影印機,很方便,這些書就整本影印下來研究。處理博士論文的時候,幾乎沒有甚麼前例可援。先前的確有些人研究過耶穌會翻譯的《伊索寓言》,可是一來幾乎沒有人懂拉丁文,二來他們對於教會的證道文化其實也不懂。他們純粹把伊索故事拿出來,說某一本書是最早中譯的《伊索寓言》,談得並不深入。殊不知在古希臘時代,《伊索寓言》是雄辯(oration)或演講時引用例證的參考手冊,壓根兒不是兒童文學。
到了天主教時代,希臘這個傳統就變成證道傳統,因為證道也是一種雄辯或演講術,所以他們就把古希臘的模式與傳統,移入天主教文化,天主教再帶來中國。因此,我們才看得到這些本非天主教文學的小故事,而且故事多到要我寫一本通史都覺得很難。後來我一直在做的都是古典型證道故事。本來我對希臘羅馬的戲劇和神話就頗感興趣,對於當時人物如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凱撒,或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也讀得津津有味,所以博士論文就專注在古典型證道故事上面。一路耕耘了幾十年,到目前為止,嚴格說來只出了三本專書,還好有一點厚度。19
單德興
讀者從書裏可以看出引證的細膩。就翻譯的角度來說,發掘歷史的考證,尤其是一些文本的源流,要是沒有讀得那麼廣,不一定找得到。另外就是歷史的訓練,也就是歷史感。還有一點就是,你也熟悉當代翻譯理論,雖然在行文中未必那麼明顯運用或炫學,但可以看出一些翻譯理論,尤其是翻譯史,已經融入其中。
李奭學
對,我的研究基本上還是放在比較文學的脈絡裏。我的比較文學定義中,翻譯占相當大的比例。我個人覺得,沒有翻譯就沒有比較文學。
單德興
我們這點看法完全一致。
李奭學
我會去查考譯出來的故事的源流,也會去拿源流來比對文中講述的這個故事,看看原文和中文重現之間有甚麼異同?一個故事來到中國之後,影響中國人又到甚麼程度?以前很少人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就覺得自己應該下點工夫去做。博士論文後來用中文重寫,成果就是《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我重寫了比博士論文多了一倍以上的篇幅,增添的兩章中,一章談古典神話,另一章談古典傳說。神話與傳說其實很難分,但為了論述上方便,只好這樣分了。我現在跟幾位助理正在把一些明清之際翻成中文的故事蒐集起來,透過各種脈絡(context)鏡考源流,但能成功處理的,還是相當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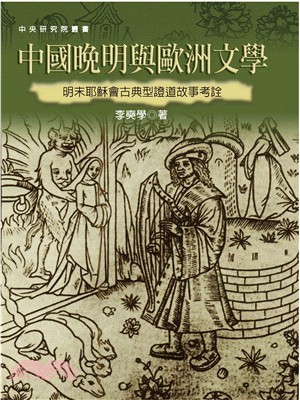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 (2005)書影
單德興
在胡適講座現場,我也問過你這個問題。大家只看到你找到的結果,我則希望你能分享所用的方法。
李奭學
最早的時候是笨方法。就是看到亞歷山大的一條故事,就找一本原典性的亞歷山大的傳記來讀。找不到的話,就看傳記裏面提到跟亞歷山大相關的其他原典。有英文的最好,沒有英文的,法文也行。還好很多有英文,也有拉丁文的著作。這是笨方法,但《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幾乎都用這種笨方法寫出來的。
單德興
地毯式搜尋。
李奭學
對,所以我開玩笑說,我在做洋考證;只是讀的人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在做。這是最早的階段。後來我跟梅謙立(Thierry Meynard)合作,英譯了明末耶穌會士高一志的《達道紀言》,20 這是一本多達六百多條的世說故事集。梅謙立小我十歲左右,他是法國耶穌會士,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大概在二○○一、二年的時候,他可能是看了一些我發表的東西,就到中研院來找我,希望能夠合作,我說可以。梅謙立最早是在李達三( John J. Deeney)畢業的那間復旦大學(Fordam University)教書,後來跑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現在是哲學系博士班的主持人。他的中、英文不錯,拉丁文非常好,因為是神父出身,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也都行,會不會葡萄牙文我沒問他,不過應該也行,希臘文更不在話下。他的古典語文訓練非常好。他跟我進一步追,跟我說可以用關鍵字(keyword)在谷歌上蒐尋。我發覺效果比原先好多了,查出了不少東西來。
話說回來,像《達道紀言》這本多達六百條的證道故事集,最多也只查到兩百多條而已,已經沒辦法繼續查下去了。我們花了十年,翻譯出來,只能說把找到的源流盡量交代出來。我們只找故事的原典,譬如色諾芬(Xenophon)的某一本歷史書等。可是耶穌會不一定是從色諾芬的歷史典籍裏尋得用例,有很多故事有很強的中世紀傳統。中世紀證道傳統大盛,神父把證道要用的故事蒐集起來,變成一本本的故事彙編,或是我們中文所謂的掌故叢談。這種書中世紀已經很多了,文藝復興時期還保留這些中世紀的傳統。
可以想像,一個傳教士來到中國,可以講出那麼多古希臘、古羅馬,還有本教前賢的一些東西,都是因為手上有這類handbooks for preaching(講道手冊)。據我所知,中世紀有兩、三千種 handbooks。這類東西,我們在東方找起來就很難了。即使人在歐洲,也沒辦法找齊,只能找到甚麼算甚麼。現在這類書我研究多了,所以相關比較重要的源頭之作大概都看過。我的助理手上非得有一套洛布叢書(Loeb Library)不可,通常我看到甚麼東西就跟助理說,洛布叢書裏面會有,去查查看。
我身邊現在有三位助理,都是從零開始訓練起。其中一個助理本來讀神學,是基督徒,比較了解這個傳統。其他兩個來的時候是一片空白,一個是臺大中文系鄭毓瑜教授的學生,另一個畢業自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他們的英文不錯,有一位也是建中畢業的小老弟。他們有的時候整天查不到,非常氣餒。這種滋味我都受過,沒甚麼。這是死功夫,有一百個助理來做,成績就會再進一步。只有一個人做的時候,又不一樣了。等到用電腦來做,已經是公元兩千年以後的事了。我發現網路上有很多電子資料庫(e-resources),端看會不會用。
|學術翻譯之路(一):翻譯是接引
單德興
這些研究等於回到了你的第一本書,也就是一九九一年的《中西文學因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好像從那時候起,不管是比較文學、文學因緣、影響研究,你的第一本書就預兆了這條路線。
李奭學
可以這樣說,我做學問滿會去看方法論這類書。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是師門以外,影響我最大的西方學者。
單德興
你做的是硬碰硬的功夫,他做的是哲學,而且是解構,感覺上兩個距離很遙遠。
李奭學
他影響我最大的就是解構思想。他很喜歡在一篇既有的文章裏,找出裏面矛盾的地方,從這裏下手去解構整篇文章,再從整篇文章去找出意義。我幾乎每次寫文章,都會感覺自己走回德希達的老路去了。
單德興
你是甚麼時候接觸到德希達?
李奭學
一九八○年代在臺灣讀研究所就接觸了,那時候他在臺灣正紅。德希達、德.曼(Paul de Man)這些人影響我很大,尤其是德.曼所謂的寓意式閱讀(allegorical reading)。本來我到美國去想要做Faerie Queene、《西遊記》這些文本的 allegorical reading ,後來改做證道故事。一九九六年我還翻譯過一本《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Read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acan, Derrida and Kristeva),由書林出版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出版,裏面討論的三位理論家之一就是德希達,作者是潘恩(Michael Payne),他其實滿會抓重點的。我那時候在美國,翻譯過程中有問題,就打電話問他。他任教於布克納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是滿好的一所小文理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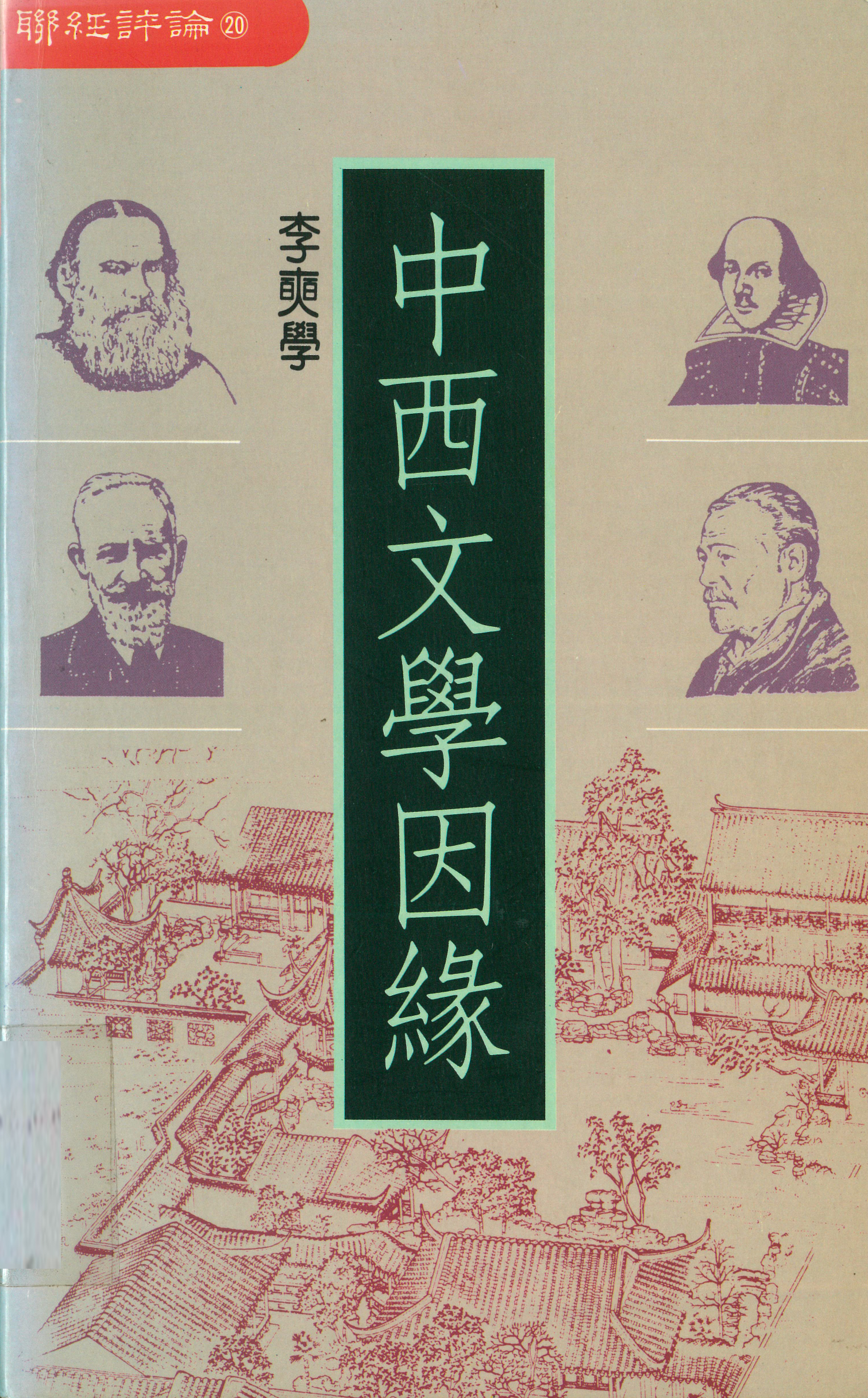

《中西文學因緣》(1991)、《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 (1996)書影
我的同學徐東風對德希達迷到極點,由德希達深入研究利瑪竇這些人帶來中國的東西。前幾天我還幫他去史語所,拍了一本利瑪竇地圖集,美國的小型大學不可能會有。這本書很小,才十八頁,是禹貢學會出版的。21 其實跟余老師寫論文,就只有我跟徐東風兩個人在明清之際逗留。徐東風因為很喜歡用德希達這套方法閱讀,所以論文寫得很慢。因為用這套方法,即使小小的文本,也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我後來花比較多的時間還是在考證,只是下筆的時候,考證的東西有時候會被我拿出來批判一下,可能對不住天主教傳統。那沒辦法,我們讀書人做學問,學術跟信仰不一定要有關係。我最近又想把古典的東西好好整理一番,不過一直在還一些債務。最近還的一筆最大的債務是欠楊牧的,你以前幫楊牧翻譯過文章。
單德興
我只翻譯過他那篇〈論一種英雄主義〉,還是大四時翻的。22
李奭學
對呀,大四,我都已經超過四十歲了喔。楊牧二○二○年去世時,還有一些文章只用英文發表。我翻譯的這篇文章是談《詩經.周頌》與舞者臉部表情之間的關係,這有點像是跳八佾舞時必須以哪一首頌歌來配合。楊牧以前是我隔壁研究室的長者,我不好推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楊牧和余國藩之間像兄弟一樣,他們的交情來自對西方古典的興趣。這篇是鄭毓瑜教授找我譯的,因為要編楊牧全集,由於編輯時程緊迫,所以一月二十八日左右我才從臺大醫院動了個小手術住院回來,大概一月三十日就開始翻譯,二月快結束時才給他們。楊牧把自己的題目都定了,叫〈周頌樂舞考索〉。23 本來還想找你問一些問題。
單德興
聽說他的博士論文The Bell and the Drum要整本重翻。
李奭學
那有得瞧了,因為《詩經》是不可捉摸的東西,意思都很難掌握。我上過一些《詩經》課,但是楊牧的《詩經》,我並不是很了解。其實我翻譯的那篇文章還滿有趣的,談〈周頌〉,會聯想到跳舞時的層次感,不容易,需要一點想像力。楊牧自己也承認,如果不用一點想像力的話,解釋不出來。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關係,所以鄭毓瑜覺得應該把這篇文章譯出來。我從醫院回來休養的時間,剛好翻譯那篇文章,結果也沒時間休息。本來我打算金盆洗手,不再翻譯東西了,因為真是花時間。
單德興
對,現在我也有這種感覺。
李奭學
我基本上是做學術性書籍的翻譯,可以從許多同行學者身上學到東西。我跟呂健忠最早翻譯《西洋文學概論》和《西洋近代文學》,24 其實發起人是我,也是我推薦給書林的。「西洋文學概論」的課,當時大家都讀諾頓(Norton)選集,很多學生讀不懂,甚至英文再好的人都讀不懂。我當學生的時候也是一知半解。後來知識漸長,對於這裏面談的各種西洋文學、時代和主義了解多了,再回想以前跟李本題讀英國文學史、跟施鐵民(David L. Steelman)讀西洋文學概論、跟柏子仁讀歐洲文學的時候,大家都望著書中的導言(introduction)興嘆。因此,翻譯《西洋文學概論》的動機只有一個,我希望用大家看得懂的話,把這些導言翻成中文,讓門外漢也能夠入門來。
呂健忠真的動手就翻譯了,他翻到某個程度的時候,看我閒閒沒事幹──其實我的事多得很!──就說你把書接完,所以我就接手完成了。之後又有《西洋近代文學》,印象中最早也是我提議的,他再讓我續完。兩本書都是這樣,後來不僅成了暢銷書,還是長銷書。因為我回美國讀書去了,呂健忠花了很多時間改編,讓初學者更容易入門,後來出版《新編西洋文學概論》,都是他的功勞。25
單德興
後來書又到大陸,二○一三年的《西方文學史》也是。26
李奭學
沒錯。那是我跟浙江大學出版社接洽,合編成一本書,不過大陸版字體比較小。
|學術翻譯之路(二)「有事,弟子服其勞」
單德興
既然提到翻譯,我們就順著這條線下來。你的學術翻譯中,翻譯余國藩的著作有《余國藩西遊記論集》、《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余國藩論學文選》。27 後來,你也翻譯了孫康宜兩部作品。
李奭學
我真的是碰巧碰到余先生的東西,那時候我已決定要到芝加哥讀書了,剛好一九八六年輔仁大學舉辦第一屆文學與宗教國際研討會。余先生的論文都是用英文寫,因為我上過康士林的《西遊記》,他就問我能不能翻譯這篇關於《西遊記》的文章。我就翻譯了,還寄回芝加哥給余先生看。他不大改動,基本上只看意思有沒有弄對。他閱讀得非常深,寫作倒是一般。後來他又寄來新作,要我幫忙翻譯。翻出來後,我就說,還有其他甚麼《西遊記》的文章都給我,我幫你轉成中文,出成集子。就在這樣的機緣下,幫余先生翻了這本《余國藩西遊記論集》,書是在我去芝加哥攻讀博士之後出的。
余先生討論《紅樓夢》那本書則是中文版先出來,在《中外文學》幾乎都發表了,只剩一、兩章還沒發表,然後英文版才出版。我一九九九年博士畢業之後, 第一年在師大翻譯所教書,簡直快忙瘋了,也沒時間把他將近十年前寫的東西補齊。等到二○○四年九月在中研院升上副研究員,我才跟余先生說,可以回來幫他補齊了。我每天在研究室翻譯到凌晨一、兩點才回家睡覺,他的英文很難譯,我只能這樣講。修辭他很在行,就英文來講,是很漂亮的英文,我總不能用隨便的中文來翻譯,所以我盡可能地用我認為漂亮的中文去翻譯。翻完之後,事情又是一大堆。我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把余先生主要的東西翻出來。
三聯書店的那本《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余國藩論學文選》,是他們主動找我的。翻譯類的書籍,著作權屬於原作者,譯文版權屬於譯者,所以他們必須先來問我同不同意,才會進一步去聯絡原作者。如果譯者不同意,就沒必要去找原作者了。三聯那本書之所以用學術論述的集子之名出版,裏面有個小小的故事。《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前面寫著獻給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死者,余先生說絕不拿掉這個悼詞。我就跟三聯說,那我來新編一本書好了,於是把他討論《紅樓夢》、《西遊記》比較重要的幾篇文章拿過來,編成新的一本書,這樣才避掉政治上的敏感性。
至於翻譯孫康宜教授的作品,是因為孫老師問余先生有沒有人能把她的書譯成中文?余先生請她問我一聲。孫老師就把余先生的名字放到給我的信上,我師命難違,於是接了。我本來不認識孫教授,後來接著把兩本書翻譯出來,她變成我亦師亦友的前輩,幫了我很多忙。《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是第一本書,28 《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是第二本。29
第一本書比較好翻,因為是一個愛情故事。孫老師有一點受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影響,想用比較漂亮的敘述方式,把陳子龍和柳如是之間的愛情,還有相關的一些詩詞介紹出來,所以那些描述不是太具技巧性。可是宋詞真的是很技術性的東西。我那時在臺灣也兼課,但沒有一個圖書館可以用,最大的圖書館就是三民書局。記得那陣子我常常在三民書局國學區找宋詞格律的書,還有她提到一些像柳永那樣的詩人的集子。我會買宋詞相關的著作,了解一些相關技術性的東西,看中文是怎麼講的,否則很可能會譯錯。孫老師很久沒有寫中文了,我譯好後寄回去給她,她一章一章從頭看到尾,想要補充就補充,稿子回到我這邊,我有的重寫了,然後再新編進去。出版的書,跟原來也有少部分不大一樣。後來我跟孫老師說,中文是妳的母語,沒那麼嚴重,就放手寫去。她後來就自己動手寫,變成作家。後來我又幫她翻譯了一篇跟中國女性相關的論文,因為她也在做性別研究。30
單德興
孫康宜後來出了精裝本全集,印刷精美,定價高昂。
李奭學
我有一套,放研究室裏。其實那套書不是要賣給一般人,是要賣給圖書館。
單德興
你認為從事學術翻譯,應該具有哪些條件或態度?
李奭學
我覺得從事學術翻譯,最好有那方面的背景。比方說宋詞,如果我不是找一些書來看,恐怕翻譯很多文句時,連名詞都會搞錯。像我們常說一「闕」詞,後來孫先生跟我說,是一「首」詞,不是一「闕」詞。雖然上半闕、下半闕是沒錯,但整體言之,還是同一「首」詞的關係。這些當然不會出現在一般談詞的書裏。因為詞是音樂和文字結合的東西,在宋朝時還有人唱詞,蘇東坡也行,跟音樂之間的關係滿密切。如果對詞的音樂背景沒有概念,會分不清一首小令跟一首長調要在甚麼場合唱,這些東西譯者自己要去了解。
余先生的書,因為我上過西方漢學家論《西遊記》的研究,自己在課堂上也把中文本的《西遊記》花了兩個月讀完,譯起來還算行。《紅樓夢》也一樣,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這樣才能抓到重點。否則光看英文,會想不出中文的脈絡是怎麼一回事。從事學術翻譯,對於所翻的東西的背景應該要有了解。若本人是個學者傾向的人,是有好處的。讀了那些背景性的書籍,會有基本的概念,下筆翻譯會有更深的體會。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訓練。就我來講,我幾乎會視之為個人訓練的一部分。這種訓練跟課堂上抓重點、講幾句話很不一樣,因為必須要讀得很細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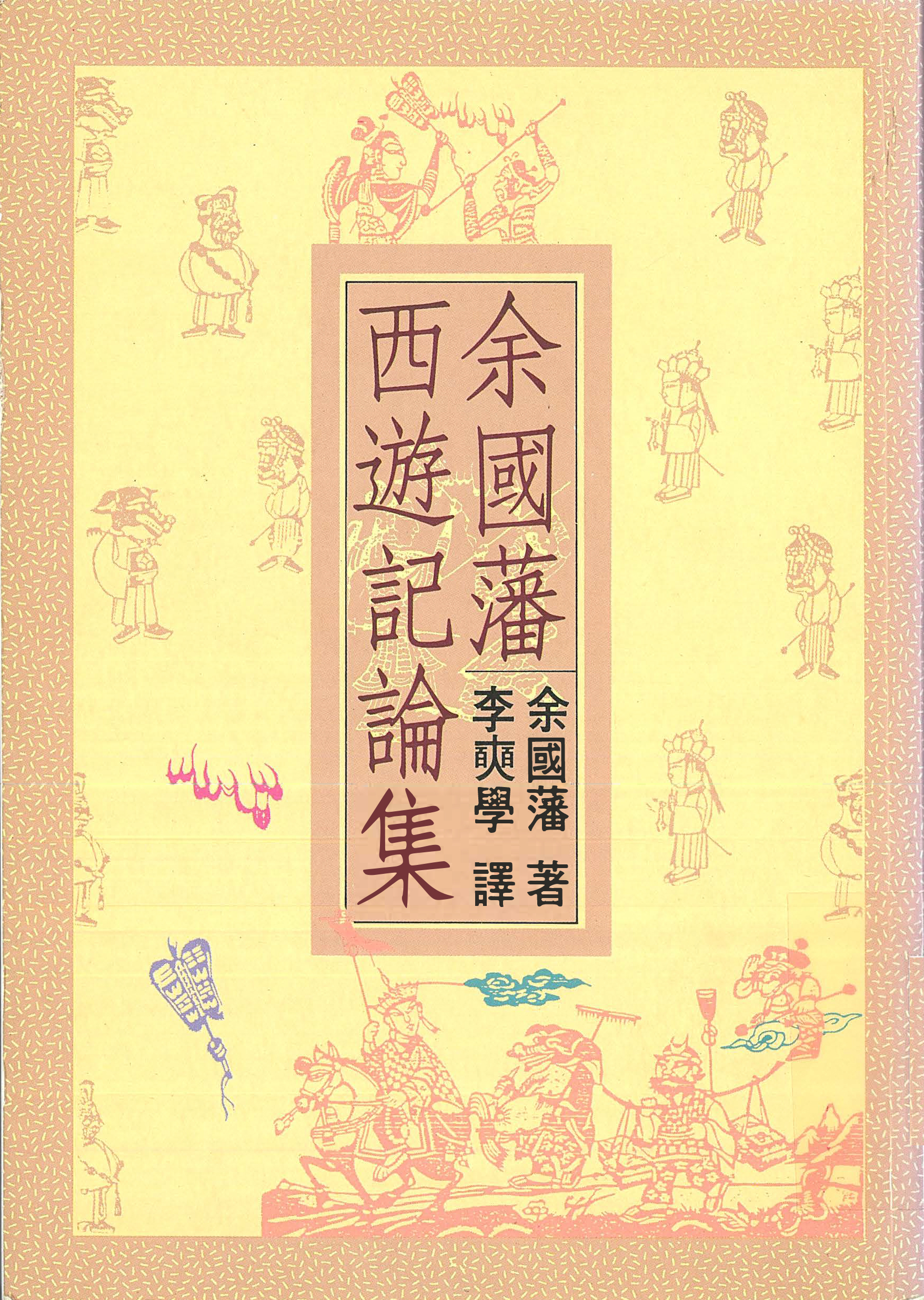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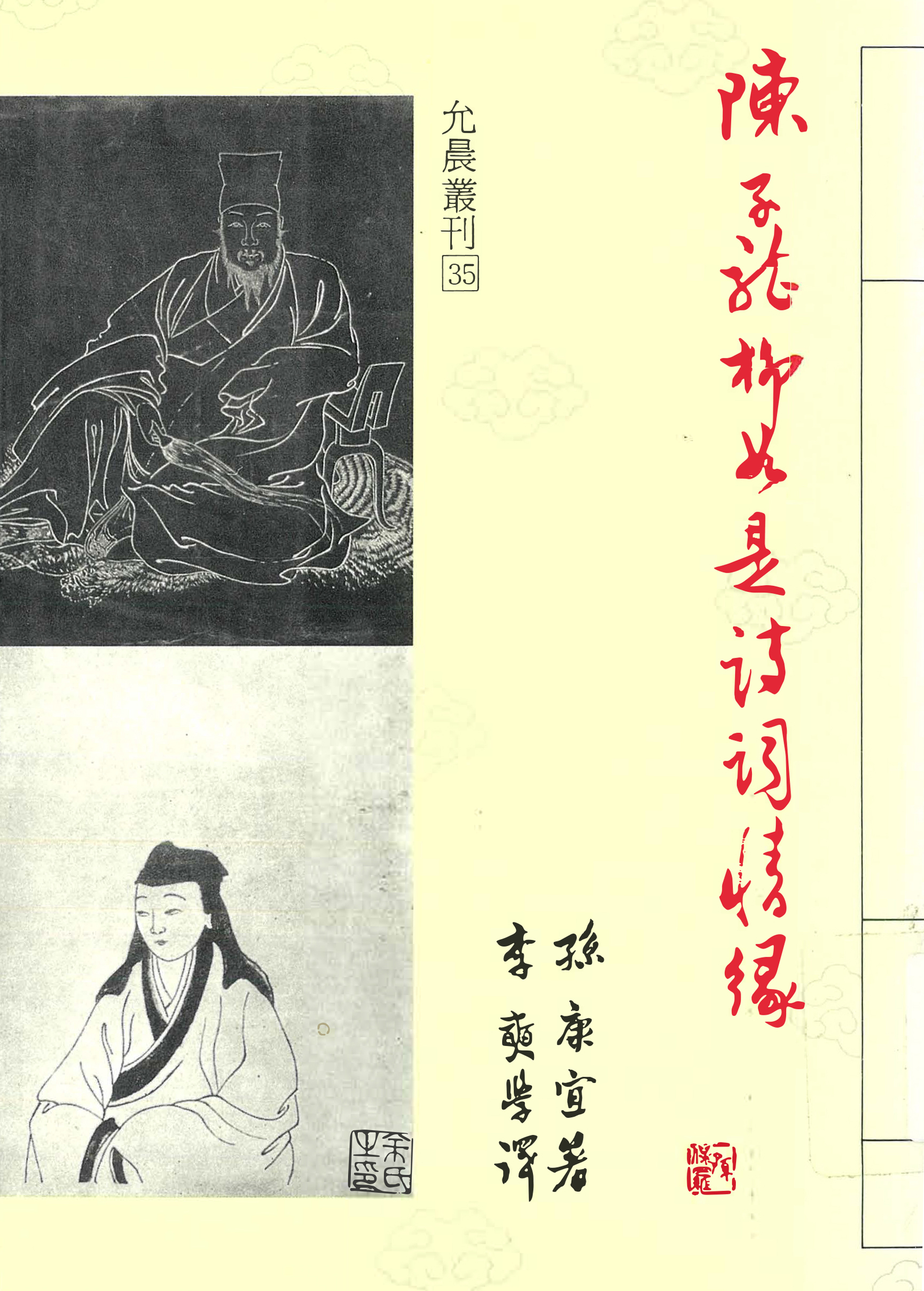
《余國藩西遊記論集》(1989)、《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1992)書影
單德興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幫他們翻譯的時候,兩位都還不是院士?
李奭學
不是。孫老師第一次提名院士,就選上了,那時候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在文學方面的院士已經有王德威、李歐梵、夏志清等人。31 余先生的時代倒還沒有文學的院士。大家一看他的資歷,芝加哥大學很有名,但余先生是神學院的人,怎麼選?然後又是個做翻譯的人,怎麼選?翻譯本來就被貶低了,大家對翻譯的誤解都很深。我記得余先生跟我說過,余英時三次提名他,前兩次被否決。他第三次申請的時候,我在芝加哥,很多資料是我幫他整理的。一九九八年七月中研院第二十二屆院士會議通過他的時候,我在臺灣,看到余國藩當選院士的跑馬燈消息,回家去拿起電話,也不管芝加哥才四、五點,就打到美國,恭喜老師當選院士。
余老師的父親是余伯泉將軍,母親歐授真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最早也是。一九三八年余先生在香港出生,父親一直在大陸帶兵作戰,因此真正的啟蒙師是祖父余芸,牛津大學畢業,國學造詣極深,當時是香港教育司署高級視學官。他從小就由祖父抱在膝上教漢字,詩詞四書五經都用廣東話讀,所以國語沒講得很好。他在香港進的也是英語學校,主要書寫語文是英文。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他十三歲時,父親於陸軍總司令部任職,才隨母親回臺灣,讀了兩年書。我聽說他先到建中,讀不下去,因為他是粵語耳朵,聽不懂國語,只好到臺北美國學校讀書,畢業後就出國了,那時應該是十七、八歲。
余先生最早是讀英國文學的,本來沒想做中文方面的學問,他的抱負全都是西方的知識。他說在去美國的船上,從一份報紙上看到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寫的一篇文章,認為這個人對中國的了解不是泛泛。因此,他那時候就在想,自己要研究西方的文史,讓西方人也認為不是泛泛,是很傑出的。他一直讀的都是西方的學問,博士論文做的是關於艾斯奇勒斯(Aeschylus)、但丁(Dante Alighieri)、米爾頓、卡繆(Albert Camus),談這幾個人的作品裏「墮落」的主題,題目就是The Fall,沒有中文本真是可惜。32 他其實有好幾篇研究西方的文章寫的很不錯。他對於希臘古典的了解非常深刻,舊教的神學比較不熟,但有關新教的神學很強。後來因為劉若愚(James J. Y. Liu)離開芝加哥大學,遠東系缺人,緊急之下問他有沒有興趣開一門跟中國相關的課。他試了一下,覺得滿有意思,才回過頭來研究中國的東西,但是西方他始終沒放棄。他寫的文章,可以看出西方古典或基督教神學的影子。
單德興
他是在哪種機緣下翻譯《西遊記》的?
李奭學
他說想要練一練英文的文筆。
單德興
練文筆不一定要翻譯《西遊記》啊。
李奭學
他跟我都有共同的經驗,我們從小都是看《西遊記》的漫畫長大的。小時候夢龍的二十四冊漫畫本《西遊記》,我不知道看了幾遍。他看的是另一個版本的漫畫。他在紐約一所大學畢業後,就到加州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畢業後就進了芝加哥神學院,成了宗教與文學(Religion and Literature)這個學科的第一屆學生。因為是宗教與文學結合在一起,在中國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西遊記》,再加上他小時候讀過《西遊記》的漫畫,印象很深刻,所以練英文文筆,很自然就拿《西遊記》來翻譯。這些都是他告訴我的。他後來對《紅樓夢》也感興趣,《紅樓夢》的研究做完之後,本來要研究《三國演義》的,可是被其他主題吸引過去,寫了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這本討論中國政教關係的書,33 接下來身體就不好了。
單德興
你幫他編過兩本專輯,一本是「余國藩教授榮退專輯」,一本是「余國藩院士紀念專輯」。34
李奭學
榮退專輯文哲所鍾彩鈞主任說要請他來,才編出來的。
單德興
那是二○○五年,他那時候是文哲所的諮詢委員了嗎?
李奭學
可能還不是。後來諮詢委員出缺,他剛好在臺灣。我們在中研院活動中心吃飯,他說杜維明找他當諮詢委員,他問我諮詢委員都在做些甚麼,我說我也不大清楚。那時候文哲所還在籌備處的階段,研究員人數不夠,聘人都由諮詢委員投票決定。
|下集請見:翻譯、文學與文化評論:李奭學教授訪談錄(下)|
1. 五穀王廟,正式名稱是「先嗇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道光年間遷建現址,五穀王、先嗇,皆指神農。
2. 該校係一九六一年由台北市萬華地區耆宿蘇穀保獨資創立。
3. 《大陸簡明英漢辭典》(Continental's Concis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編訂者為吳炳鍾,陳本立、蘇篤仁編修,一九七三年五月初版發行。
4. 此書由Hazard Adams和Leroy Searle合編,自柏拉圖一直到二十世紀,依年代順序排列,每篇之前有編者撰寫的簡介。
5. Brooks, Cleanth & Robert Penn Warren (1943) Understanding Fic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6. 根據《葉珊散文集》〈後記〉(1966),葉珊/楊牧在金門當兵時,讀完外國友人贈送的牛津版《濟慈書信全集》(頁204)。
7. Vargo, Edward P. (1973) Rainstorms and Fire: Ritual in the Novels of John Updik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8. 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文化大學。
9. Li Sher-shiueh (1985) "Fate and Fortune in the Plays of Christopher Marlowe," M.A. Thesi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0.Moody, William V. & Robert M. Lovett [莫逖、勒樊脫] (1947) 《英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柳無忌、曹鴻昭(譯)(上海:國立編譯館出版)。
11. 中央研究院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始於一九九六年七月,該年度的核定通過名單包括呂妙芬。
12. Li Sher-shiueh (1999) "Toward a Missionary Poetics in Late Ming China: The Jesuit Appropriation of 'Greco-Roman' Lore through the Medieval Tradition of European Exempl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3.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一六○八年),利瑪竇在教眾汪汝淳協助下,刊刻了《畸人十篇》,體例是問答體,內容全為友朋問道增潤而成,對話的時間地點不一,各篇引用的警喻不乏《聖經》篇章,但更常用的是西方史事和寓言,而《伊索寓言》中文版的首譯或首述者即為利氏。參閱李奭學 (1990),〈希臘寓言與明末天主教東傳初探〉,《中外文學》19.1,頁 135, 137。
14. 李奭學 (1990),〈希臘寓言與明末天主教東傳初探〉,《中外文學》19.1,頁 131-157。
15. Murrin, Michael (1969) The Veil of Allegory: Some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Allegorical Rhetoric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明熹宗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年),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口譯拉丁文本《伊索寓言》,由張賡筆述,彙為一卷,題為《況義》(即寓言),於西安府鐫行。全書共三十八則寓言,其中有二十六則來自《伊索寓言》。《況義》是中國最早的《伊索寓言》中譯本,此書有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影本收錄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2009),第四冊(臺北:利氏學社)。
17. 李奭學為一○八年度胡適紀念研究講座得獎人,於中研院一○九年知識饗宴──胡適院長科普講座發表演講「晚明耶穌會奇特的『文藝復興』──從亞歷山大大帝談起」,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18. Mack, Maynard 等 (1988)《西洋文學概論:上古迄文藝復興》,李奭學、呂健忠(編譯)(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 李奭學 (2005)《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西洋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明清西學六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20. Li Sher-shiueh & Thierry Meynard (2014) Jesuit Chreia in Late-Ming China: Two Studies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Alfonso Vagnone's Illustrations of the Grand Dao (Bern: Peter Lang).
21. 利瑪竇編繪《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北平 : 禹貢學會,1936),譯自Matteo Ricci's World-map in Chinese, 1602。
22. C. H. Wang[王靖獻] (1975)"Towards Defining a Chinese Hero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1: 25-35;單德興(譯)(1976),〈論一種英雄主義〉,《中外文學》4.11,頁28-45。翻譯此文的始末,參閱單德興 (2020),〈譯事.譯緣:我與楊牧先生的翻譯因緣〉,須文蔚(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頁73-83。
23. C. H. Wang [王靖獻] (1974)"The Countenance of the Chou: Shih Ching 266-296" (〈周頌樂舞考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2: 425-449。
24. Mack, Maynard (1990)《近代西洋文學:新古典主義迄現代》,李奭學、呂健忠(編譯)(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5. 李奭學、呂健忠(編譯)(1998)《新編西洋文學概論:上古迄文藝復興》,修訂版(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6. 李奭學、呂健忠(編譯)(2013)《西方文學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7. 余國藩(1989)《余國藩西遊記論集》,李奭學(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臺北︰麥田出版與國立編譯館,2004),譯自Anthony C. Yu, 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7);《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余國藩論學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28. 孫康宜 (1992, 1998)《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李奭學(譯)(臺北:允晨文化公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另一版本為《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英文本參閱Kang-i Sun Chang (1990) The Late-Ming Poet Chʻ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9. 孫康宜(1994)《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李奭學(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後來更名另出版了一本孫康宜著,《詞與文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30. 孫康宜(1993)〈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李奭學(譯),《中外文學》21.11: 52-81;收入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頁 134-164。
31. 上述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順序分別為:余國藩(第22屆,1998年)、李歐梵(第24屆,2002年)、王德威(第25屆,2004年)、夏志清(第26屆,2006年)、孫康宜(第31屆,2016年)。
32. Anthony C. Yu (1969) “The Fall: The Poetical and Theological Realism of Aeschylus, Milton, and Camus,” Ph.D. Dissert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33. Anthony C. Yu (2004) 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34. 李奭學(主編)(2005),「余國藩教授榮退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5.4;「余國藩院士(1938-2015)紀念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5.3 (2015)。

